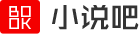p那棵柚子树是近十年来村子里生长的野史拳
那棵柚子树是近十年来村子里生长的野史。
所谓野史,就是无人照料,自由疯长,长期游离在一个村子的视野以外。当然,也可以理解成:一棵树的生长,没有人在场。不难判断,一棵柚子树从幼苗长成顶天立地的大树,十年足够了。它生长的地方,是表哥倒塌的房屋废墟。这个被我多次放进文学世界度量命运的表哥,一生未娶,漂泊南方,最后落得客死故乡。之所以是客死故乡而不是异乡,由于他回乡断气时,自己的房屋早已沦陷得不剩一片瓦砾。也就是说,柚子树最初的生长大概可以追朔到一个时间 在那个可靠的时间里,一个人的离去与归来,再到消失,这棵柚子树心知肚明。
它一定不是人为栽种的柚子树,我想说它是无主人看管的野树。可它又是村子里的幸运之树,因为它获得想怎么长就怎么长的自由,没有丝毫风险。很可能是村落里吃柚子的人不经意落下的一粒籽。但那个吃柚子的人,或许早已不知去向,柚子树是否还想着那个面目全非的人?
这只有柚子树心里最清楚。
发现这棵柚子树是一个升懒腰的晨后。当我正要将手从空中放下,一声 椭 地特别响、非常近,忽然将我视线直接拉到柚子树下。那一刻,我感受了大地的弹性与引力,和地球的不确定性。真够奇异,难道是树上的柚子在以这种方式向我打招呼吗?同时,我又想,这枚柚子是不是太沉不住气了?它是因为等来人烟气息来才落地的吗?仔细一看,地上已零星躺着十多枚形状并不特殊的柚子,有的已严重腐烂,但我一眼认出了那个刚落地的大柚子,它有着新鲜的青黄皮肤,睡在沟里的姿态,与那些先落地的柚子格格不入。
我蹲下身,抱起了它。然后,抬头望向这棵柚子树。在它庞大的体积里,还显现有十多枚柚子,有的藏匿在浓枝淡叶处,有的攀升到离天最近的地方。它们随时都有落地的自由,看样子,它们还在听候时间的指令,并且我相信,它们有自主的选择,由于它们在自然的规律里生存与腐朽,一年又一年。
本来打算将这一枚自由落体的柚子带回城里,但母亲表示了嗤之以鼻的反对。其理由是这棵在她眼皮底下视而不见的柚子树是棵废树,它结的柚子,虽大个,但味道不正宗,村子里的鸟儿也不愿多光顾。更重要的是,母亲担心这一枚野树结下的柚子,如果随着我进城,破坏村庄名声的可能性极大。母亲不愿我从村庄里带走的柚子,让城里的人说不甜。但我又想,很多时候,村庄遗弃的东西,往往容易成为城里稀缺的宝贝。母亲阻挠不了我,劝我还是先验证一回再作决定。我用清水洗尽皮肤上沾满雨露与霖迹的这枚柚子,同时也洗掉鸟兽落下的粪便与脚痕,拿刀将它剖腹,看柚蕊色彩,这属于红星柚。
双手终究取出一个瘤子状的大家伙,然后再分成一把把梳子,撕开梳子的一层粉色护膜,先试着尝了大口,再用舌尖顶了顶,发现它缺的不是水,而是水太多,野水野,少糖蜜,野水解不了家渴。
这怪不了柚子树的知在。
村落时间
回村落的时间一年比一年少。
碰到一些人,但也有很多人未能碰上面。太多人不知去向,虽然都清楚,彼此还活在世上,但谁也不会主动提出,要找一个时间,郑重其事地回村庄碰面。
村落还能够给予我们甚么?
村落至少可以找到我们最初出发的时间。
一棵树,一片叶,一朵雪,一只鸟,一声吠,一口井,一粒麦子,一株玉米,一把稻穗,一节高粱,一地花生,1首歌谣,乃至一条巷子的发迹,都是地点见证的凭据。
尽管我们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换了一个又一个,可村庄一直在静止的时间里,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在各自的天涯,把对方弄丢。
之后,没有谁去找寻谁。
其实我们轻而易举就能要到对方,只是我们要不到对方时间。我们的时间,一头停在故乡的村庄,一头停在他人的城市,中间是丘陵或山峰阻隔的微弱信号。很多时候,城市因浮肿切断了村落的信号,村落时间,让我们这些身在外头飘荡的人,一无所知。
有时,我想,即使同学一场,那怕在一起只有几个月,或几天时光,也会产生碰面的动机。而且这样的碰面,时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然而,村落与校园的情感刻度完全不同,10多年的邻居,而且我们算得上发小,论情感基础,它可以胜过我们走出村庄重新构建的所有世界。但自从别后,村落里的有些人,注定再也没有碰面机会。
2十多年都是这样。
时间是村庄从容的贩毒份子,它若无其事地将大亩大亩的作物毒死,人也随那些死去的庄稼而死,村庄里的人愈来愈少,但谁也抓不住时间的把柄。虽然我们各自都在努力,总逾越不了时间的圈套。时间给我们定制了相处的情感,又要逼迫我们分别,然后不留余地偷走我们渴望碰面的机会,直到我们再也说不出再见。
不管我多久回来一次,都不用奢侈碰面这事儿。走在故乡长满丝茅草的路上,偶尔会遇到一些熟习的面孔,顺便问起那些碰不到面的人。然而,得到的回答,多少还是有些兴趣。比如谁谁谁在广东打工又生了一个娃,据说前不久还开着车回来过。
无意中,那个碰不到面的人,就会通过他人把自己的消息装进我脑子。可碰不到面的人,始终不在场,进入脑子里的消息,因碰不到面而发酵,如何拓展想象,总要费些时间 他落实二胎计划比国家政策来得早一些,大的那个孩子该上中学了吧,他的两个孩子都长得什么样?还是像他小时候瘦高个,营养不良,爱上火起疙瘩流鼻血吗?
据他家父说,他带着两个孩子和女人,从广州展转到上海,开始新的人生发展,他们把一部分足迹留给广州,而属于他们的村落时间将被上海彻底冻结。这是我母亲不经意泄漏的消息。
我已很久没有问起过他,由于问了也是白问。人在外头,走过的城与留下的村庄,最终只能尘归尘,土归土。自从他的母亲离世后,他的村庄时间随之停在另一个世界的念想里,可信的是 谁也偷不走我们血液里曾流淌的村庄时间。
有时,我会忽然萌发一个惊喜 有那么一天,他会不会在离村庄那末远的上海早晨,想起我们曾经共有的村庄,然后忽然冲动地打一个长途给自己家父问起我?他并没有忘记我们的村落时间。但很快,我便掩耳盗铃地持了否定态度。上海时间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无论广州,还是上海,他接受的只可能是密度高于村庄的高速信息生活,情感之水滴不进他密不透风的城墙死缝。
村庄时间究竟还能给予走出村庄的人什么?
也许,一生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分别。
人与人的分别,人和一个地名的分别,人同情感的分别,遗憾的是村落并没有赋予我们分别的经验。
我们第一次尝试到村庄时间之于出走者的重量。
霜冷芭蕉
故乡有芭蕉,但不成林,三两株同稀疏的丘陵人家一样,落寞但不孤单,炊烟与鸟儿就是最好的陪伴。
房前屋后竹篱堆上耸立的芭蕉树,若是夏天,看上去还是很风光。不管刮风下雨,芭蕉叶子发出的声音都很强势,至少它不是一个弱者,在我的聆听中,它比其他物种更有胆识和魄力。在风抵达之前,它的姿态已经完全处于痛迎,内心涌动狂乱的张扬,成片的竹林尖尖发出动乱的信号,片片芭蕉如同扇子摇摆得狗吠声声,村落不得安宁。
之于芭蕉叶形状就没必要过量叙述了,可以想象一下《西游记》里,牛魔王的妻子铁扇公主手上的武器,更加直观印象是人们爱好吃的羊排,而且是双排,也具有芭蕉叶茎脉的密度。论象形,芭蕉叶可用一个 非 字解构,无论是手绘、油画、还是国画,很多画家笔下都曾有雨打芭蕉的浸染与润饰,看上去随便廖廓几笔,我几次拿笔照葫芦画瓢,其实不容易到位。
酷暑与雨季,我曾将芭蕉叶用来当伞。而村庄人的生活用处就多了,遇谁家的喜事宰杀宴请,肉块下面都会铺上宽大的芭蕉叶,而高高的蒸笼底下更会垫上一块裁剪得当的芭蕉叶,无论是酒米饭还是酥肉,都会散发更加沁人肺腑的清香。
芭蕉树的主脉特别壮,由一层一层的苞皮构成,水份相当充满。小时候,我亲眼见过水田的二爷将削得尖尖的竹筒子,扎进芭蕉树身体取水喂牛解渴,原来是他们家的牛中了毒,用芭蕉水为动物解毒,功效相当神奇。这是被很多农村挺进城市的人遗忘的村落史!
谁遗忘了村庄里的这等生活细节,谁就将过早成为被幸福遗弃的人。
村庄里最美的花应该是芭蕉树的花。这是村落人很难承认的美之发现。因为芭蕉树本来就高达三四米,那些花就像空中绽放的礼花,而且是世界上最黄的花,即便白天,它们也比黑夜灿烂,没有在黑夜里仰望过幸福的人,怎么能懂白天的灿烂?我观察过芭蕉开花后光阴残留的苞片,犹如猪八戒粉色的耳朵,有一定的柔韧性,像一块质量不错的胶皮,药用价值不低。
1棵芭蕉树的花苞似一头牛的心脏,沉甸又肥实。
真正出自故乡的香蕉,我吃得并不多,一是产量本来就少,再者有点就用来看病人或拿去卖了当家补,能吃上香蕉的人家,在旧年的丘陵少之又少。故乡的香蕉,多是成熟前放进稻草堆里捂过的,有点见不得人的出土文物表情。除了品相很难与水果店里华丽光鲜的香蕉比,味道绝对有得一拼 粉甜、饱满、黏稠、香涩,甚至充满了蜜汁的况味。
少年的芭蕉,总是葱葱郁郁,生机勃勃,把房舍点缀得似乎永久是春天。那种绿,简直就是一座村落的标志,同时也是一方天空的表达方式。然而步入中年,偶尔一见芭蕉,藏在丘陵中的故乡,总是陷入霜冷的萧瑟,看上去没精打采。
仔细查找缘由,故乡人去楼空是一种难以更改的现状,有人说这是农村的进步,芭蕉独自摇曳的孤独无人能懂也是一种现状,宋朝的李清照说这是一种离愁,南方丝竹乐《雨打芭蕉》表现的是哀婉与别绪,除了李清照,南唐后主词人李昱笔下也有同等意味的书写,作为永远的返乡者我不再借物抒愁,即便是秋末蕉叶凋零,故乡无人再为蕉剪枯叶,壅土护根,失去稻草的包扎,芭蕉基部有的已经冻结、或腐烂,好比失散的亲情,或一个经年无人过问的流浪汉。根上长出的幼株明显少了,分株繁殖的事情没有人干了,霜冷芭蕉成了村庄的一种宿命写照,那么肥厚的叶片不再泛绿,而是时刻处于紧张、焦灼、燃烧的地步,稍不留神就可能被风带走。
由此不难发现,1座村庄的灭亡是从芭蕉树的腐烂开始的,同样,1座村庄的复苏,也可以从芭蕉树开始,由于芭蕉的温性更需要人气的热忱护卫,它不是植物中的野性派呀!
动脉硬化日常保健方法男性长期便秘的危害
新疆白癜风病是怎么来的
- 06月21日二次元科达布犬的外形特征及生活习性位置
- 06月21日二次元秋田犬产后不吃食物怎么办位置
- 06月21日二次元秋田犬不喜欢睡狗窝要怎么办位置
- 06月21日二次元研究发现狗狗喘息是在笑位置
- 06月20日二次元可卡犬怎么算年龄位置
- 06月20日二次元可卡多少钱一只可卡的外貌尤为漂亮位置
- 06月20日二次元可以给雪纳瑞犬吃鸡肝吗位置
- 06月20日二次元可以用脱毛霜给贵宾犬拔耳毛吗位置
- 06月20日二次元可以喂茶杯犬吃什么水果知识位置
- 06月20日二次元可卡犬会和主人情久生相位置
- 06月20日二次元可卡犬产后如何护理知识位置
- 06月13日二次元先询问一下哈士奇关于哈士奇的喂养和其他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