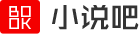女生网
光棍节的前一夜(1)
光棍节的前一夜,夜色的寒光刺得城市的公园里的青草不敢抬头,勇敢的虫鸣被时不时的机动车的呼啸给打压,安蜜尔在那一夜借着悠然的月色喝掉了近一箱啤酒,她右手的五根手指被纱布包着,因为捏着酒瓶时用力过猛,纱布在不知不觉的变红,月色的惨淡和她手指上猩红产生了锋利的联结,周身从未那般寂静过。 你们怎么都像个娘们,叫你们喝个酒真困难。 。
这是她完全醉倒之前对着两个大男人说得最后一句听着尚在逻辑内的话,后来她的身体完全被酒精给钳制了,嘴上含糊的说着些脏话痞话,每当我总习惯把救助的眼光投向身边的阿城,他是个喜欢摇滚和摄影的长胡子男人,当然,相较前者来说,我认为他更喜欢安蜜尔。所以当安蜜尔醉得不省人事时他总是最焦急的,他一焦急起来就手足无措,事情都办的毫无条理,就像那晚安蜜尔趴在公园的草地上呼呼大睡的时候,他居然将车钥匙一把抢了过来,将死猪样的安蜜尔硬生生扛进了后座,然后不等我打开车门上车他就丢给我一个满是红色血丝的目光,那是恐吓我吗?每次遇见这样的事情和如此的目光时我都害怕的自问,再然后车被他开走了,我面对着一桌子的酒和零食欲哭无泪。
光棍节是我的受难日,一点也没错,但绝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单身的原因,更多的是那俩好朋友都是有情人,不过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每年的光棍节他们都会在大白天和的另一半做完一切能做的事情,然后看似心地善良实则满腹毒水的将夜晚的留给我,每一年都是在这个叫做 马克公园 的地方喝酒,聊天,主要是批斗我的洁身自好,在我无力辩驳之后他们再开始将自己种种文不对题的观灌输给我,鼓励我好好的去开始一场恋爱,过程中基本上是安蜜尔在喋喋不休,清澈透亮的声音在夜晚黑色的空气中特别的迷人,每次她对我柔柔细语或是狂轰滥炸时我其实都保持一种面上抵触心里享受的姿态,你是我,你可以从她的嗓音发出的迷人魅力中发掘女人纯粹的一面,也是一种越来越稀有的特质。阿城会吃醋,就算是我他都会吃醋。他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搞不懂的男人。安蜜尔也不是不知道阿城对她的意思,但是她就是装作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每天依旧和他插科打诨,胡言乱语。阿城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几次我从不经意的间隙发现了阿城的心痛,看得我有些不忍心,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就是一个胖得无可救药,长相平凡的键盘手,除了在音乐上我能够有些虚空的自信之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球,在我面前越滚越绚丽晶莹,美好的东西在不时的打击我,音乐,唯有这个老朋友能够陪着我在生活中保持安定。
再说到那晚的酒局,安蜜尔醉了后被阿城扛到了车上,阿城丢给我一个恐吓的眼神后开着我的二手车扬长而去,剩下的一堆烂摊子我也懒得收拾,当我拿着最后一瓶酒起身时桌上一堆垃圾袋后突然发出嗡嗡嗡的声音,是阿城的手机。我拿起手机清楚的看见屏幕上邬靖靖三个字有些为难,不知道该不该帮阿城糊弄糊弄,出于朋友之间的情谊我的确应该帮,可一想到那个混蛋扛着安蜜尔开车就走我难免有些心气不顺,想了想我还是决定接起来。
这明显是个问句,明显到我都能够听出她话语后面的那个大大的问号,想来想去还是不要说太多实话比较好,能糊弄一会算一会。
看来这个小妮子是要刨根问底, 在啊,当然在,我们仨难得忙里偷闲喝会酒,她现在喝得跟死猪一样,睡在我家沙发上不走了,要不要她跟你说句话?
我知道,这不用我问他,他这不今天晚上就匆匆忙忙回去帮你准备礼物去了吗?连酒都不敢多喝。
我边摸着额头上的冷汗,边对着城子的手机笑着。小姑娘呵呵呵的笑声终于让我的心放了下来,我匆匆和她寒暄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马上把手机关了。
秋天还走,清冷的星空将我盖在了下面,我忽然有一种压抑感,不知为何。城子的手机在口袋里被我的手汗濡湿,邬靖靖的声音像是垂吊在银河的一颗星石,慢慢的下沉下沉,怎么也落不到地表,可我居然会有种被星石砸眩晕感。
清早的寒意逼人,不知不觉十二月这个月份进入了我的生活。我习惯大早起床开一壶水,然后架着小梯子从阁楼上拿出一小瓶的铁观音,轻轻的捏一点在手里,小瓶子里的茶叶眼看着一天天的减少,每一次抓的时候都有种心疼的感觉。而在十二月的第一天的清早,由于茶叶也快喝完,瓶子里仅有的些许茶叶被我的手指慢慢的挑弄,生怕多抓了一丝,就在我费劲力气调整好手指间的分量时,我脚下的小梯子终于不堪重负的断了,从我踩着的那一阶开始断,我的脚被地心引力疯狂的吸引,往下落的过程中踩断了下面的两根木头,这不是关键,关键的是我落在了一盆仙人掌里,那是我养了好几年已经产生浓烈的感情的植物,我爱护他们像是爱护自己之前的女朋友,在我没有落进去之前我笃定的相信他们比上任何一个女人值得获得我的宠爱,但当我的屁股和后背重重的落在了里面,我清楚的听到了细微的声响,不知道是刺扎进我***的声音还是我把它压瘪的声音,总之我痛到喊不出来甚至差点晕厥,就此我对它也失望了,流血尽管是必然的,我没有想到关键时刻我对它们的百般爱戴居然换不回一点心软,该死的。
最后没想到茶叶也落得一地,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坐在地上崩溃的大哭,生怕声音小了一点表达不了我的心内的悲伤,哭的时候其实心里和身体是没有痛感的,我享受着这种歇斯底里带来的麻木,至少能给我减缓疼痛。
我果断拒绝了医生给我提出的住院观察的这个建议,简单的做个包扎开了点药就回了家。自从上次城子把车开走再还给我后,这两破大众已经开始对我无限的不满,时不时的在路上罢工,时不时的不听使唤,无论我是多么急切的需要它的帮助,就像我忍着屁股上锥心的疼痛在马路上等红灯时,它突然熄火了。绿灯亮起很久了它依然像是没看见似的原地不动,任凭我用尽吃奶的力气踩油门,它还是一动不动。身后的千军万马已经蓄势待发,配合着屁股上的刺痛感我差点掏出车上那把生锈的水果刀在车内自尽,交警终于向我走来,其余的车辆已经绕道而行,我听得出那些车在路过我的时候喇叭里的愤怒。我要下车窗看着那个大冷天还带着墨镜耍酷的男人,他问我怎么回事,我慌乱起来就不会说话,东扯西扯好不容易把原因讲出个大概时,他已经开始掏兜,我想没必要吧,又不是故意影响交通秩序,要惩罚也不能罚我吧,正当我想开口理论时一个女人走了过来,那是冬日晌午暖和的阳光,懒洋洋的铺在她身上时我感觉我是看到了人间的仙女,虽然仙女的脸上也架着副墨镜,身上的制服款式并不是那么合适她的气质。美,终究是美,无论什么丑恶在其上面胡乱作怪,始终是遮挡不了其中的美。就像是那个女交警,她走近的时候我才发现所有的崩溃和绝望都是为了与美相遇的铺垫,继而,命运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巴掌。
我一刹那感受到了什么叫想挖个地洞把自己埋了的心情,手上的方向盘一打滑配合脚上的习惯动作,本以为它的机动性已经偃旗息鼓,谁知道这时候他又十分配合的冲了出去,手掌心的汗水已经把方向盘给打湿,一会的功夫两个交警已经出现在了我的后视镜里,他们脸上的神情从冷酷到惊愕就像是跑车加速,不过几秒钟的事,我不好意思的把车停了下来,想着如果要有什么惩罚我也认了。
朋友多就是好办事,邬靖靖几句话的事就把我从那个满脸凶恶的交警队长面前放走了,走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了她对着我的车屁股一笑,或者说是对着我微微一笑,我不敢再往下幻想了,开车在宽敞又拥堵的路上让我不得不克制内心的不安,这一天所经历的一切,让我十足疲惫。
疲惫就算再强大,为了生活还是要振作起来,这不是我一贯的风格,但就在我安全到家的时候房东的电话打了过来,催着我看看日历,如果没钱买日历下次他劝我去楼下的垃圾场捡一个日历,说话一向刻薄尖酸的老女人这次几乎是声嘶力竭,到最后甚至对我发出来最后的通牒,如果月底不拿出两个月的房租,她就要把我的东西扔进垃圾场,把我也扔进去。一想到那个满头黄发,右手手背上有一朵花样纹身的中年女人,每次抽着烟斜眼瞟我的样子,我浑身上下就颤抖起来,所以我顾不上屁股上的伤口和家里满地的狼藉,一个电话打给了阿城,阿城说今晚有活。
赶到城南的1947酒吧我屁股上的痛感已经麻木,走起路来只是感觉屁股上湿湿的,粘粘的。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化脓了,当我在门口的阴影中小心的用手摸着屁股时阿城在里面对我大喊了一声,门口的几个原本没发现我的女孩惊讶的冲我一笑,我的手连忙从裤子里缩了出来,一个穿着 制服的女孩发现了我手上的小动作,眼睛里的羞涩刻意的在绚彩的灯光中舞弄着,我一个箭步冲了进去。
台上安蜜儿唱得无比投入,台下的反响不错。站在台边的赞歌一脸陶醉的样子,阿城说 看来老板又要给蜜儿涨工资了。 可不是吗?1947就靠蜜儿能撑撑场面了。这不是好事吗? 我端起吧台上的威士忌一饮而尽,刚喝下去我忽然想起医生对我忌辣忌冷的忠告,一点醉意立马涌上来了,我迷迷糊糊的望着台上的安蜜儿,阿城一转眼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坐在台下我突然想唱歌了,安蜜儿那首《安眠药》唱的我有些心痒,我又向服务员要了一杯威士忌,赞哥这时候走了过来, 哥们,酒可不是白喝的。 知道,赞老板,我们这么多年不都贴着你干嘛。
白天公司的事有些忙,一下忙不过来,这段时间过去就没事了,到那时候我天天晚上来捧您的场子。
我始终没有忘记我不是一个纯粹的音乐人,我正式的职业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每天白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拉保险,晚上跟着蜜儿和阿城去城南的一家小酒吧唱歌,我忽然想起当初和阿城说到组乐队的这个想法时还得到了阿城的嘲笑,阿城说我不务正业,当时阿城是投资公司的顾问,收入不菲,虽然时不时的会玩一玩音乐,却没打算真正的在音乐上有什么作为,后来我说服蜜儿,我们三个成了一个乐队,到现在阿城辞掉工作专心跟着赞哥做乐队,蜜儿也是,我没想到我到头来成了一个生活在与现实的夹缝中的男人,想到这里我看着赞哥陶醉的脸,心里不知其味。
到了下一首该我上场了,蜜儿对我抛了个媚眼,台上却没见阿城的身影。蜜儿小声说 没贝斯,你慢点弹。
音乐声起,我的身心在音乐中沉淀下来,刚才的醉意慢慢散去,剩下的事耳蜗中清亮的嗓音了婉转的琴声,一首终了我看见台下的赞哥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然后蜜儿向台下走去,我成了台上的唯一焦点,我把那首我唱了许多年的歌再次在舞台上唱起, 像疯了一样,越想你九月心伤,我多么爱你,却难逃你的魔掌。
舞台正对面的落地窗出现了一个女人,我慢慢唱着副歌,像是隔着一段不远的距离和一扇落地窗诉说着隐秘的心情,那个女人的脸上出现了泪光,彩色的霓虹遮蔽了我焦急的目光,歌曲到了高潮部分,窗外的场景如同一出音乐剧,配上歌声后我感觉我不再是那个懦弱的男人,不等赞哥和蜜儿在台下给我鼓掌我往台下一跳,那个穿着学生制服的女生显然被吓了一跳。
在大家的喧哗中我冲到了屋外,那扇落地窗前一切像是什么都发生,又像是发生了一切。那个女人蹲在地上抽泣,来来往往的男女没人注意这太过庸常的细节,月光再次充当了天使,我一时间是不敢呼吸的,那份勇敢在那一刻还未来临,一抬头月亮笑了,我慢慢启动步子往落地窗走去。
我轻轻楼主她的肩膀,她的肩膀抖得厉害,她没有抬头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我该死的心跳出卖了我,这就是她身上的香气吗?我不懂得什么香水,但是我知道这种香味并不是香水能够装饰出来的气息,时她本该有得体味,天啊,我居然第一次不顾周遭人们的各色眼光做出了这样肉麻的举动,后来仔细回想确实有些心急。
如果不是赞哥和蜜儿,我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一声叫得我直哆嗦,怀里的邬靖靖立马推开了我,她的眼睛里除开泪水就剩愕然了,我承认当时的我确实不太理智,但是等我想理智的时候就只剩下一个解释的机会了,那不是最糟糕的结果吗?我自问了许久,对着邬靖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个冬天不太冷的周末,阳光给了大家一个热情洋溢的笑容,就在我无所事事的时候被蜜儿叫到了城南的1947,谁知道打扮得跟日本美少女一样的她一看口就是如此语重心长的一句劝告,然后点燃了一只烟,朝我丢了一根后吐出了一口烟圈。
你都多大了,认识你那么久了也没见你有个异性朋友,当然除了我之外。 她喝了一口咖啡,眼睛里含着看不到底的深井, 谁知道你不鸣则已,一鸣是要逼死谁啊。
我不知道对她的嘲讽是该摆出一副真爱无敌的态度呢,还是应该和她插科打诨转开话题,犹豫间赞哥走了过来,赞哥递给我一杯咖啡, 哥们,挺前卫,挺开放的,看不出来呀。
我一笑就让蜜儿又抓住了机会 还笑,还有脸笑,你觉得你二十大几岁快奔三十的人没女朋友挺光荣的是吧?
我起身拿起包就准备走,不知道为什么蜜儿每次的讽刺都能直接打到我的心内最柔软的那一层,所以避免我自己再受伤害,也避免我和她的关系出现什么裂痕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走。
我们俩不知不觉走到了护城河边,前几天下过场雪,河面上结了薄薄的一层冰,人们在河岸上享受生活的悠闲,我和她找了个地方坐下,蜜儿说的话慢慢在我的脑子里练成了一幅幅图像。
光棍节前一夜,马克公园里我们几个酩酊大醉,蜜儿被阿城用我的车劫走了,我在醉意中听见了阿城的手机响了,邬靖靖再电话里的几句话我记得不清楚,但是我记得她特意叮嘱我让我问问阿城光棍节的第二天是什么日子,想到这里我大概明白了前因。
蜜儿说 邬靖靖这女的作,之前好几次明里暗里的说我是狐狸精我就当作没听见没看见,不跟她一般见识,还真当我是个智障脑瘫似的。
和以往的所有的纪念日一样,能够料想得到的是,阿城那种具有文艺情怀的浪子心怎会把一个稀疏平常的日子当作一件事来对待呢?还不说是什么头等大事,邬靖靖又是个特别在意细节的女人,一个不留心就会让她大哭大闹,把所有值得的不值得的事情弄得一发不可收拾,阿城和她的个性在我分析,没有一处能够完美匹配。
我想起前一晚我对邬靖靖夸下的海口,突然有些惭愧内疚。 阿城第二天没给她一点惊喜,似乎给了她一叠惊吓。
那天我想应该也是一个晴天,蜜儿拿着杯咖啡到阿城去找他,看蜜儿一副可怜的样子我无条件相信,她是去找阿城改编一首晚上需要演出的情歌的,敲门的时候阿城在里面忙活了半天才又回应,蜜儿当时以为邬靖靖也在里面,本来马上就准备走,门突然打开了。阿城穿着浴袍头发湿漉漉的模样叫蜜儿吓了一跳。
蜜儿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在下咽一口滚烫的咖啡,然后那口咖啡被卡在了我的喉头,随即喷到了一个过路人的脸上。
俩人进去了后开始聊这首歌曲,阿城看蜜儿这么主动找他便一进门就开始和她商量讨论,根本忘记了换衣服这件事,身上的大浴袍和头上的水珠一切的一切都在酝酿一次战争前肃杀的烟雾。不等人们察觉,战争的号角吹响,敲门声打乱了他们热火朝天得讨论。蜜儿说那天下午确是激发灵感的时候,谁知道一阵敲门声切断了她和阿城的思绪,她说她恨不得隔着门超外面骂一句 操。。。。。。
蜜儿坐得离门口比较近,推开桌子气冲冲用屁股顶开椅子冲到了门口,准备了一副不耐烦的表情给门口打扰她的人,谁知道门打开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邬靖靖手里的花落了一地,落下来的还有一个盒子,棕色长盒子在花瓣中格外像是一具棺木,瞬间那种悲凉的氛围就起了,蜜儿顿时懵了,阿城听见门口一阵声响后安静了许久,便走到门口去看。没人想到如果阿城不出现两个女人之间的沉默会对峙多久,阿城以一袭浴袍出现时门口的邬靖靖控制不住的哭了,坐在门口嚎啕大哭,蜜儿说那种哭声是一般人不能承受的哭声,好像一听到这种哭声就知道地狱之门的方向了。我不知道她这是什么比喻,总之邬靖靖在门口哭得很惨,我想象不到当时邬靖靖的模样,在我的印象中她整体来看还是非常有淑女的气质,只是时不时的神经质而已,阿城喝醉之后曾对我们诉说邬靖靖的各种撒泼,蜜儿一副看的样子,我却不敢相信。
蜜儿说 哭完闹完,我准备走的时候她一把扯住我的手臂,你知道啊,她一个女交警劲儿大啊,我的胳膊根本动不得,阿城过来准备拉住她,你知道她说说了句什么?
蜜儿不光把语气模仿出来,连眼睛翻动的频率都学了出来,我有些畏惧的看着蜜儿,我感觉心里一个美好的形象正在蜜儿这个屠夫手下慢慢瓦解。
你是不知道她当初那傻样,我真是恨不得上去抽她一耳光。当然,阿城帮我出了口气,上去就是一耳光把她扇倒在地。
面对一个怨妇你要怎么解释?你给我解释解释看看,你说得倒轻巧,她那样蛮不讲理一上来就扯我胳膊我还要怎么礼貌?
我们俩坐在护城河边吹风,因为一两句的争执彼此都沉默了很久,阳光在中午的时候将护城河上的冰晒化了,我准备对蜜儿说句对不起,转眼看蜜儿低头拿着手机不知在干什么,我不知怎么开口才好。当我准备开口的时候蜜儿突然抬头对我说 出事了,出事了,赞哥被人打了,1947被人砸了。
我没反应过来就被蜜儿拖到了出租车上,她坐在后座焦急的握着手机,我一路叫司机加快速度,加快速度。蜜儿问我要不要打电话给阿城?我说到时候去了再说吧。
一路飞驰,车停在1947门口时我惊呆了,门口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几个警察在门口打电话,两辆警车停在后视镜里,我和蜜儿都有些不敢下车。
警察手中的塑料袋里装着凶手作案的蒙古刀,刀上还染着血迹。蜜儿一下倒在了我的怀里,警察说 先叫救护车,你是老板什么人?
我记得那天蜜儿被送上救护车后我有些眩晕,跟着警察到了酒吧里面的厨房,赞哥的一摊血迹还在地上,白净透亮的地板砖被一滩渗人的血红给霸占,像是一种无声的宣告,我被那一摊血迹给刺杀了,日后许多的日子里我都回不过神来,做梦梦见他还是小时候的样子,带着我满山奔跑,给我抓蛐蛐,蚂蚱,蜻蜓,我还记得我最爱的那只竹蜻蜓现在还摆在我的床头,只是我不记得他从什么时候长大的,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只为利益而不顾情谊的男人,从父母去世以后?从祖父将他赶出家门之后?还是从祖父离去我也只身一人来到城市以后?我那时才发现,原来他不是长大,也不是变化,只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已,而我学不会这样的保护,所以我需要他时不时对我的帮助,这样我才能更顺利的在这座并不欢迎我的城市中生活下去,当初我只是想要一份工作,没想到他却为了我努力开了一家酒吧,他为了我的梦想而付出了自己的心血,我没有为他而付出什么,当我接到医院的死亡通知单,我知道我之前所有的费解以及因为费解而生成的怨恨和抵抗都被一纸通知碾成了灰烬。
蜜儿住院了,医生说她严重贫血。无奈之下,蜜儿的爸妈从老家赶了过来,来的那天蜜儿还在生我的气,怪我瞒着她几把她爸妈叫了过来,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也懒得再解释什么。赞哥,她始终有些不相信,她说赞哥是个好人,就算是和她谈了恋爱也没有想过做什么过分的事情,不像有些风流鬼。我还未从赞哥的死亡中清醒过来,蜜儿看样子倒也没那么伤心,我想问的问题一直没有问出口,犹疑间病房的门被推开了,蜜儿的爸妈大包小包的进来了,我礼貌的打了招呼就出了门,不管蜜儿怎么对我使眼色我都出来了,我不习惯别人家的热闹和温暖,再有,我又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南方一下起雨来没有尽头似的,整个城市都湿漉漉的,我开车准备去往警察局的路上突然想起了邬靖靖,电话打通后邬靖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问她最近怎么了?问出口就后悔了,蜜儿才告诉我她自从那天的纪念日风波后一直萎靡不振。邬靖靖没吭声,我下意识问她她在干嘛,她的呼吸正准备带出一句话时电话断了,我的直觉中邬靖靖一定是遇到了困难,阿城的影子在我潜意识里带着模糊的光影,不管了,我将方向盘打回来,一路加速开往邬靖靖的家。
城北的烟草厂的小区里弯弯曲曲的小路太多,这一片全是年代感极强的老房子,邬靖靖家我只来过一次,还是几年前阿城生日邬靖靖邀请大家一起去她家给阿城庆生,阿城那天穿着别扭的西装,打着红色领带,远远看过去像个新郎官。蜜儿调侃他是个乡下暴发户。
我沿着小院子的左侧围墙走着,一只黑猫不知何时从旁边的小绿化带里窜了出来,停在我脚边时我推了一步,往后往前看了一眼发现居然没有,甚至没有一点声音。城市的喧闹一点没有在此体现,我装作凶恶的样子对着那只老黑猫跺了跺脚,吓得它又钻进了绿化带。后来到达邬靖靖家楼下才想起赞哥曾说过 如果遇见黑色的猫,别吓它,它不会怕你。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想得越多害怕得越多,进了楼梯间潮湿的台阶上出奇的滑,我记得是三楼的左手边,门上的缝隙里插着不知那年那月的艾蒿叶子,敲门的时候发现门居然没关,推开门口屋子里的黑暗叫人窒息,窗帘拉得死死的,不透一点光亮。邬靖靖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呼呼睡着,桌上的鲜花和长方形礼盒摆在茶几上,我轻轻打开礼盒,在打开礼盒前我走到窗户前拉开了窗帘,打开了窗户。盒子里呈放着一条手帕,手帕上写着 蒙古工艺 四个字,背面写着成串的蒙古文。
她撑起身子以一个慵懒的姿态仰面坐在沙发上,我环顾客厅里整齐干净,完全像是一个独居的女性的房间,她伸手向沙发侧面的箱子里,艰难的拿上来一瓶八宝粥递给我,我疑惑她的有气无力,她说 不好意思,家里只剩这个了。
她惊恐的把脚从地上缩到了沙发上,两条长腿弯曲在身前,下巴重重的放在膝盖上。像个不懂事的小女孩。
谁知道我这句话一出口她抱着一瓶八宝粥就哭起来了,我连忙接过她手里马上就要滑落的八宝粥,给她递上了那块手帕。
你知道我为了给他准备一个纪念日礼物,我把我所有的家底都花了,我爸现在在老家做心脏搭桥手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拿起那个长方形礼盒发现里面有张证书,我才想起原来礼物并不是什么手帕,而是一把蒙古刀。阿城确有收藏各种工艺刀的爱好,他曾说过他如果不做音乐他就会去开一个有关刀具的工艺品商店,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不敢再往下想象。
我不敢相信朝夕相处的阿城会对一个女人做如此粗鲁的事,邬靖靖的家里冷得要命,坐了一会我手就冰得吓人。她的手放到了我的手上说 你是不是冷?我去拿火炉。
我没准备把赞哥的死告诉她,她本应拥有一个专心诚挚的爱人,和她一样美好纯净的爱情,她不应该再经受任何现实给她的伤害,死亡是有种莫可名状的力量的,像段枯木被打进了心底,根本拔不出来。
我起身走时看见了她丢在茶几一角的两只袜子,我捡起两只白色的袜子转身过来时她已经睡着了,我走到她身边给两只冻得僵硬的脚套上,她脸上的安宁是大起大落后疲倦的缩影,我想我应该去为他讨回一些什么,我的心随着她怀中的胎儿的震动而沸腾起来,俯身正面她时她脸上的细节都摆在了我的眼睛里,细致的皮肤,毛孔,因为长久失眠生成的眼袋和黑眼圈,嘴唇是她最性感的地方,唇上的皱褶干裂了,渗出了血,血结了痂。
我关上门后并没有因为后悔放弃了一个亲吻她的机会而沮丧不已,现在的我需要理智来进行任何一项行动,下楼之后下起了雪子,一粒粒冰晶砸在脸上刺痛得让人颤栗。
梦做了许久,醒来后头痛欲裂,梦里的情节记不清一二,窗外的树梢上经过一夜的风雪满是雪白,树枝被压弯了身躯,玻璃上氤氲的雾气迷蒙,我伸手轻轻在玻璃上化了一张笑脸,屋外的银装素裹的景色透过一道明净的缝隙,我在成年之后有时不太喜欢大雪,喜欢阳光的时候比喜欢大雪要多得多。
雪夜,我根本顾不上有什么不妥,1947的一切都是属于我和他的,还有蜜儿,阿城。屋外的大雪没有停息的意思,风小了些,我从里面紧紧锁上门,把大厅里的灯全部打开,舞台上的灯亮起来的时候我几乎在一时间看见了当初第一次登上台的我,旁边是阿城疯狂的摇晃脑袋,舞台中的蜜儿甜蜜美好,和她的名字一样叫人对她不得心生爱慕。
我把柜台里的酒都拿了出来,酒不多了,摆在吧台上像极了一排排炸弹,我决定今夜我要尽全力喝下它们,它们是他留给我的遗物,如果不喝下它们,我不知道还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我对他的亏欠。
一杯接一杯,我想酒醉的午夜不来一些音乐根本不配来宿醉一场,从吧椅上下来时碰倒了桌上的一瓶芝华士,玻璃碎裂在地上的声音刺进了我的大脑,刚在迷迷糊糊中获取了些自在和洒脱,恍然清醒了过来,我立马端起了桌上的酒杯一饮而尽,我至今记不起我是怎么爬上了舞台,舞台上的话筒和话筒架的位置没有改变,我特意去摸了摸键盘,上面覆盖着一层灰尘。
齐秦的这首老歌是我多年来最爱的一首情歌,每次唱起它我就会想起一些凌乱又温柔的往昔,不过这次我借着醉意又一次在这个舞台哼起来时,我的眼前全是第一次的画面。
第一次来1947,第一次对赞哥说我要组乐队,第一次带着阿城和蜜儿来1947,赞哥配合我演了一出没有结局的戏码,第一次从阿城和蜜儿的眼睛里看见对音乐对梦想的渴求和希望,那时的我觉得无比满足,1947是我们三人追逐梦想的开始,我无法接受如今大家分崩离析的事实,酒劲在我的体内像一股比一股强劲的潮涌,拍打我的胸腔中最为软弱的地带。
我喷出了胃里未消化的秽物,躺倒在舞台中央,头上的五彩霓虹盖住了我的脸,我的身体,音乐还在耳边回荡,我能够想象窗外的大雪如何将整座本就冷漠的城市慢慢埋葬,冬天就此宣告降临,人们终究在孤独中掩饰孤独,世界在清冷的冬天成了一座孤独的宫殿,我准备慢慢睡去,以后如果还有机会醒来的话。
台下隐约的脚步声将我从梦中拉回,侧身面对台下一个模糊的人影,我对所有的鬼魂早已免疫了最恐怖的一面,渐渐地那个人影开始对我鼓掌,对我呼喊,我的意识里他应该不会是赞哥,如果是他他就会在台下大喊让我站起身来,然后再上来拥抱我。
睡过去后我忘记了一切,梦中我又回到了那个大雪纷飞的清晨,我对着雾气氤氲的玻璃窗滑下了一个简单的笑脸后,蜜儿打了电话给我,说阿城找了她,她说阿城现在像鬼一样落魄。找到她的时候阿城几天没有进食,在小饭馆里吃了十个馒头和一桶米饭,蜜儿当时被眼前这个饿死鬼一般的男人吓住了,然后他对蜜儿表白了,蜜儿在电话里说起这段恶心的表白差点呕吐。
蜜儿说她已经和阿城已经约好时间,晚上1947见。原来阿城这几天并没有在外逃亡,而是躲在1947的一个藏酒的地窖里,那个地窖联通着后门,从后门出来就是一片菜地,菜地几乎没有人去,阿城白天从菜地里挖些野菜,晚上偷溜倒厨房想办法弄熟它们。
蜜儿和我说完这些我不敢相信,不敢相信阿城居然真的成了一个丧心病狂的杀人犯,虽然在想象中我一度想过这种可能,不过等现实出现在面前时我还是无法面对,蜜儿说 阿城疯了,彻底疯了,廖儿,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害怕,我生怕他把我生吞了。
雪融化的第一天中午,我和蜜儿再一次坐到了护城河边,护城河的河水清灵灵的,有几只小渔船在远处飘摇,风吹散了树梢上的雪堆,散到了蜜儿的脖子里她抓住我的手臂直叫。
她瘪了瘪嘴,阳光依旧不肯放过亲吻她的脸颊,河边的风都被太阳照暖了,我眯起眼睛望向天空南归的燕子,它们从我们的头顶滑翔而过,一点没有离去时的伤心。
我不准备回答她这个问题,我也懒得追问她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秘密的。从兜里掏出一包彩苏,递给她一根,她看我不回答的气势有些赌气,接上烟后把头偏了过去。
烟点上了以后我觉得我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废人,前段时间我从自卑的心境中好不容易抽身而出,谁知道这么美好的氛围里再次被它拖了下去,我现在只想问出那个我没有对她问出的问题。河南治疗男科方法腿部淤青发紫怎么消除儿童咳嗽常吃的止咳药
这是她完全醉倒之前对着两个大男人说得最后一句听着尚在逻辑内的话,后来她的身体完全被酒精给钳制了,嘴上含糊的说着些脏话痞话,每当我总习惯把救助的眼光投向身边的阿城,他是个喜欢摇滚和摄影的长胡子男人,当然,相较前者来说,我认为他更喜欢安蜜尔。所以当安蜜尔醉得不省人事时他总是最焦急的,他一焦急起来就手足无措,事情都办的毫无条理,就像那晚安蜜尔趴在公园的草地上呼呼大睡的时候,他居然将车钥匙一把抢了过来,将死猪样的安蜜尔硬生生扛进了后座,然后不等我打开车门上车他就丢给我一个满是红色血丝的目光,那是恐吓我吗?每次遇见这样的事情和如此的目光时我都害怕的自问,再然后车被他开走了,我面对着一桌子的酒和零食欲哭无泪。
光棍节是我的受难日,一点也没错,但绝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单身的原因,更多的是那俩好朋友都是有情人,不过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每年的光棍节他们都会在大白天和的另一半做完一切能做的事情,然后看似心地善良实则满腹毒水的将夜晚的留给我,每一年都是在这个叫做 马克公园 的地方喝酒,聊天,主要是批斗我的洁身自好,在我无力辩驳之后他们再开始将自己种种文不对题的观灌输给我,鼓励我好好的去开始一场恋爱,过程中基本上是安蜜尔在喋喋不休,清澈透亮的声音在夜晚黑色的空气中特别的迷人,每次她对我柔柔细语或是狂轰滥炸时我其实都保持一种面上抵触心里享受的姿态,你是我,你可以从她的嗓音发出的迷人魅力中发掘女人纯粹的一面,也是一种越来越稀有的特质。阿城会吃醋,就算是我他都会吃醋。他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搞不懂的男人。安蜜尔也不是不知道阿城对她的意思,但是她就是装作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每天依旧和他插科打诨,胡言乱语。阿城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几次我从不经意的间隙发现了阿城的心痛,看得我有些不忍心,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就是一个胖得无可救药,长相平凡的键盘手,除了在音乐上我能够有些虚空的自信之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球,在我面前越滚越绚丽晶莹,美好的东西在不时的打击我,音乐,唯有这个老朋友能够陪着我在生活中保持安定。
再说到那晚的酒局,安蜜尔醉了后被阿城扛到了车上,阿城丢给我一个恐吓的眼神后开着我的二手车扬长而去,剩下的一堆烂摊子我也懒得收拾,当我拿着最后一瓶酒起身时桌上一堆垃圾袋后突然发出嗡嗡嗡的声音,是阿城的手机。我拿起手机清楚的看见屏幕上邬靖靖三个字有些为难,不知道该不该帮阿城糊弄糊弄,出于朋友之间的情谊我的确应该帮,可一想到那个混蛋扛着安蜜尔开车就走我难免有些心气不顺,想了想我还是决定接起来。
这明显是个问句,明显到我都能够听出她话语后面的那个大大的问号,想来想去还是不要说太多实话比较好,能糊弄一会算一会。
看来这个小妮子是要刨根问底, 在啊,当然在,我们仨难得忙里偷闲喝会酒,她现在喝得跟死猪一样,睡在我家沙发上不走了,要不要她跟你说句话?
我知道,这不用我问他,他这不今天晚上就匆匆忙忙回去帮你准备礼物去了吗?连酒都不敢多喝。
我边摸着额头上的冷汗,边对着城子的手机笑着。小姑娘呵呵呵的笑声终于让我的心放了下来,我匆匆和她寒暄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马上把手机关了。
秋天还走,清冷的星空将我盖在了下面,我忽然有一种压抑感,不知为何。城子的手机在口袋里被我的手汗濡湿,邬靖靖的声音像是垂吊在银河的一颗星石,慢慢的下沉下沉,怎么也落不到地表,可我居然会有种被星石砸眩晕感。
清早的寒意逼人,不知不觉十二月这个月份进入了我的生活。我习惯大早起床开一壶水,然后架着小梯子从阁楼上拿出一小瓶的铁观音,轻轻的捏一点在手里,小瓶子里的茶叶眼看着一天天的减少,每一次抓的时候都有种心疼的感觉。而在十二月的第一天的清早,由于茶叶也快喝完,瓶子里仅有的些许茶叶被我的手指慢慢的挑弄,生怕多抓了一丝,就在我费劲力气调整好手指间的分量时,我脚下的小梯子终于不堪重负的断了,从我踩着的那一阶开始断,我的脚被地心引力疯狂的吸引,往下落的过程中踩断了下面的两根木头,这不是关键,关键的是我落在了一盆仙人掌里,那是我养了好几年已经产生浓烈的感情的植物,我爱护他们像是爱护自己之前的女朋友,在我没有落进去之前我笃定的相信他们比上任何一个女人值得获得我的宠爱,但当我的屁股和后背重重的落在了里面,我清楚的听到了细微的声响,不知道是刺扎进我***的声音还是我把它压瘪的声音,总之我痛到喊不出来甚至差点晕厥,就此我对它也失望了,流血尽管是必然的,我没有想到关键时刻我对它们的百般爱戴居然换不回一点心软,该死的。
最后没想到茶叶也落得一地,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坐在地上崩溃的大哭,生怕声音小了一点表达不了我的心内的悲伤,哭的时候其实心里和身体是没有痛感的,我享受着这种歇斯底里带来的麻木,至少能给我减缓疼痛。
我果断拒绝了医生给我提出的住院观察的这个建议,简单的做个包扎开了点药就回了家。自从上次城子把车开走再还给我后,这两破大众已经开始对我无限的不满,时不时的在路上罢工,时不时的不听使唤,无论我是多么急切的需要它的帮助,就像我忍着屁股上锥心的疼痛在马路上等红灯时,它突然熄火了。绿灯亮起很久了它依然像是没看见似的原地不动,任凭我用尽吃奶的力气踩油门,它还是一动不动。身后的千军万马已经蓄势待发,配合着屁股上的刺痛感我差点掏出车上那把生锈的水果刀在车内自尽,交警终于向我走来,其余的车辆已经绕道而行,我听得出那些车在路过我的时候喇叭里的愤怒。我要下车窗看着那个大冷天还带着墨镜耍酷的男人,他问我怎么回事,我慌乱起来就不会说话,东扯西扯好不容易把原因讲出个大概时,他已经开始掏兜,我想没必要吧,又不是故意影响交通秩序,要惩罚也不能罚我吧,正当我想开口理论时一个女人走了过来,那是冬日晌午暖和的阳光,懒洋洋的铺在她身上时我感觉我是看到了人间的仙女,虽然仙女的脸上也架着副墨镜,身上的制服款式并不是那么合适她的气质。美,终究是美,无论什么丑恶在其上面胡乱作怪,始终是遮挡不了其中的美。就像是那个女交警,她走近的时候我才发现所有的崩溃和绝望都是为了与美相遇的铺垫,继而,命运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巴掌。
我一刹那感受到了什么叫想挖个地洞把自己埋了的心情,手上的方向盘一打滑配合脚上的习惯动作,本以为它的机动性已经偃旗息鼓,谁知道这时候他又十分配合的冲了出去,手掌心的汗水已经把方向盘给打湿,一会的功夫两个交警已经出现在了我的后视镜里,他们脸上的神情从冷酷到惊愕就像是跑车加速,不过几秒钟的事,我不好意思的把车停了下来,想着如果要有什么惩罚我也认了。
朋友多就是好办事,邬靖靖几句话的事就把我从那个满脸凶恶的交警队长面前放走了,走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了她对着我的车屁股一笑,或者说是对着我微微一笑,我不敢再往下幻想了,开车在宽敞又拥堵的路上让我不得不克制内心的不安,这一天所经历的一切,让我十足疲惫。
疲惫就算再强大,为了生活还是要振作起来,这不是我一贯的风格,但就在我安全到家的时候房东的电话打了过来,催着我看看日历,如果没钱买日历下次他劝我去楼下的垃圾场捡一个日历,说话一向刻薄尖酸的老女人这次几乎是声嘶力竭,到最后甚至对我发出来最后的通牒,如果月底不拿出两个月的房租,她就要把我的东西扔进垃圾场,把我也扔进去。一想到那个满头黄发,右手手背上有一朵花样纹身的中年女人,每次抽着烟斜眼瞟我的样子,我浑身上下就颤抖起来,所以我顾不上屁股上的伤口和家里满地的狼藉,一个电话打给了阿城,阿城说今晚有活。
赶到城南的1947酒吧我屁股上的痛感已经麻木,走起路来只是感觉屁股上湿湿的,粘粘的。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化脓了,当我在门口的阴影中小心的用手摸着屁股时阿城在里面对我大喊了一声,门口的几个原本没发现我的女孩惊讶的冲我一笑,我的手连忙从裤子里缩了出来,一个穿着 制服的女孩发现了我手上的小动作,眼睛里的羞涩刻意的在绚彩的灯光中舞弄着,我一个箭步冲了进去。
台上安蜜儿唱得无比投入,台下的反响不错。站在台边的赞歌一脸陶醉的样子,阿城说 看来老板又要给蜜儿涨工资了。 可不是吗?1947就靠蜜儿能撑撑场面了。这不是好事吗? 我端起吧台上的威士忌一饮而尽,刚喝下去我忽然想起医生对我忌辣忌冷的忠告,一点醉意立马涌上来了,我迷迷糊糊的望着台上的安蜜儿,阿城一转眼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坐在台下我突然想唱歌了,安蜜儿那首《安眠药》唱的我有些心痒,我又向服务员要了一杯威士忌,赞哥这时候走了过来, 哥们,酒可不是白喝的。 知道,赞老板,我们这么多年不都贴着你干嘛。
白天公司的事有些忙,一下忙不过来,这段时间过去就没事了,到那时候我天天晚上来捧您的场子。
我始终没有忘记我不是一个纯粹的音乐人,我正式的职业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每天白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拉保险,晚上跟着蜜儿和阿城去城南的一家小酒吧唱歌,我忽然想起当初和阿城说到组乐队的这个想法时还得到了阿城的嘲笑,阿城说我不务正业,当时阿城是投资公司的顾问,收入不菲,虽然时不时的会玩一玩音乐,却没打算真正的在音乐上有什么作为,后来我说服蜜儿,我们三个成了一个乐队,到现在阿城辞掉工作专心跟着赞哥做乐队,蜜儿也是,我没想到我到头来成了一个生活在与现实的夹缝中的男人,想到这里我看着赞哥陶醉的脸,心里不知其味。
到了下一首该我上场了,蜜儿对我抛了个媚眼,台上却没见阿城的身影。蜜儿小声说 没贝斯,你慢点弹。
音乐声起,我的身心在音乐中沉淀下来,刚才的醉意慢慢散去,剩下的事耳蜗中清亮的嗓音了婉转的琴声,一首终了我看见台下的赞哥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然后蜜儿向台下走去,我成了台上的唯一焦点,我把那首我唱了许多年的歌再次在舞台上唱起, 像疯了一样,越想你九月心伤,我多么爱你,却难逃你的魔掌。
舞台正对面的落地窗出现了一个女人,我慢慢唱着副歌,像是隔着一段不远的距离和一扇落地窗诉说着隐秘的心情,那个女人的脸上出现了泪光,彩色的霓虹遮蔽了我焦急的目光,歌曲到了高潮部分,窗外的场景如同一出音乐剧,配上歌声后我感觉我不再是那个懦弱的男人,不等赞哥和蜜儿在台下给我鼓掌我往台下一跳,那个穿着学生制服的女生显然被吓了一跳。
在大家的喧哗中我冲到了屋外,那扇落地窗前一切像是什么都发生,又像是发生了一切。那个女人蹲在地上抽泣,来来往往的男女没人注意这太过庸常的细节,月光再次充当了天使,我一时间是不敢呼吸的,那份勇敢在那一刻还未来临,一抬头月亮笑了,我慢慢启动步子往落地窗走去。
我轻轻楼主她的肩膀,她的肩膀抖得厉害,她没有抬头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我该死的心跳出卖了我,这就是她身上的香气吗?我不懂得什么香水,但是我知道这种香味并不是香水能够装饰出来的气息,时她本该有得体味,天啊,我居然第一次不顾周遭人们的各色眼光做出了这样肉麻的举动,后来仔细回想确实有些心急。
如果不是赞哥和蜜儿,我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一声叫得我直哆嗦,怀里的邬靖靖立马推开了我,她的眼睛里除开泪水就剩愕然了,我承认当时的我确实不太理智,但是等我想理智的时候就只剩下一个解释的机会了,那不是最糟糕的结果吗?我自问了许久,对着邬靖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个冬天不太冷的周末,阳光给了大家一个热情洋溢的笑容,就在我无所事事的时候被蜜儿叫到了城南的1947,谁知道打扮得跟日本美少女一样的她一看口就是如此语重心长的一句劝告,然后点燃了一只烟,朝我丢了一根后吐出了一口烟圈。
你都多大了,认识你那么久了也没见你有个异性朋友,当然除了我之外。 她喝了一口咖啡,眼睛里含着看不到底的深井, 谁知道你不鸣则已,一鸣是要逼死谁啊。
我不知道对她的嘲讽是该摆出一副真爱无敌的态度呢,还是应该和她插科打诨转开话题,犹豫间赞哥走了过来,赞哥递给我一杯咖啡, 哥们,挺前卫,挺开放的,看不出来呀。
我一笑就让蜜儿又抓住了机会 还笑,还有脸笑,你觉得你二十大几岁快奔三十的人没女朋友挺光荣的是吧?
我起身拿起包就准备走,不知道为什么蜜儿每次的讽刺都能直接打到我的心内最柔软的那一层,所以避免我自己再受伤害,也避免我和她的关系出现什么裂痕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走。
我们俩不知不觉走到了护城河边,前几天下过场雪,河面上结了薄薄的一层冰,人们在河岸上享受生活的悠闲,我和她找了个地方坐下,蜜儿说的话慢慢在我的脑子里练成了一幅幅图像。
光棍节前一夜,马克公园里我们几个酩酊大醉,蜜儿被阿城用我的车劫走了,我在醉意中听见了阿城的手机响了,邬靖靖再电话里的几句话我记得不清楚,但是我记得她特意叮嘱我让我问问阿城光棍节的第二天是什么日子,想到这里我大概明白了前因。
蜜儿说 邬靖靖这女的作,之前好几次明里暗里的说我是狐狸精我就当作没听见没看见,不跟她一般见识,还真当我是个智障脑瘫似的。
和以往的所有的纪念日一样,能够料想得到的是,阿城那种具有文艺情怀的浪子心怎会把一个稀疏平常的日子当作一件事来对待呢?还不说是什么头等大事,邬靖靖又是个特别在意细节的女人,一个不留心就会让她大哭大闹,把所有值得的不值得的事情弄得一发不可收拾,阿城和她的个性在我分析,没有一处能够完美匹配。
我想起前一晚我对邬靖靖夸下的海口,突然有些惭愧内疚。 阿城第二天没给她一点惊喜,似乎给了她一叠惊吓。
那天我想应该也是一个晴天,蜜儿拿着杯咖啡到阿城去找他,看蜜儿一副可怜的样子我无条件相信,她是去找阿城改编一首晚上需要演出的情歌的,敲门的时候阿城在里面忙活了半天才又回应,蜜儿当时以为邬靖靖也在里面,本来马上就准备走,门突然打开了。阿城穿着浴袍头发湿漉漉的模样叫蜜儿吓了一跳。
蜜儿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在下咽一口滚烫的咖啡,然后那口咖啡被卡在了我的喉头,随即喷到了一个过路人的脸上。
俩人进去了后开始聊这首歌曲,阿城看蜜儿这么主动找他便一进门就开始和她商量讨论,根本忘记了换衣服这件事,身上的大浴袍和头上的水珠一切的一切都在酝酿一次战争前肃杀的烟雾。不等人们察觉,战争的号角吹响,敲门声打乱了他们热火朝天得讨论。蜜儿说那天下午确是激发灵感的时候,谁知道一阵敲门声切断了她和阿城的思绪,她说她恨不得隔着门超外面骂一句 操。。。。。。
蜜儿坐得离门口比较近,推开桌子气冲冲用屁股顶开椅子冲到了门口,准备了一副不耐烦的表情给门口打扰她的人,谁知道门打开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邬靖靖手里的花落了一地,落下来的还有一个盒子,棕色长盒子在花瓣中格外像是一具棺木,瞬间那种悲凉的氛围就起了,蜜儿顿时懵了,阿城听见门口一阵声响后安静了许久,便走到门口去看。没人想到如果阿城不出现两个女人之间的沉默会对峙多久,阿城以一袭浴袍出现时门口的邬靖靖控制不住的哭了,坐在门口嚎啕大哭,蜜儿说那种哭声是一般人不能承受的哭声,好像一听到这种哭声就知道地狱之门的方向了。我不知道她这是什么比喻,总之邬靖靖在门口哭得很惨,我想象不到当时邬靖靖的模样,在我的印象中她整体来看还是非常有淑女的气质,只是时不时的神经质而已,阿城喝醉之后曾对我们诉说邬靖靖的各种撒泼,蜜儿一副看的样子,我却不敢相信。
蜜儿说 哭完闹完,我准备走的时候她一把扯住我的手臂,你知道啊,她一个女交警劲儿大啊,我的胳膊根本动不得,阿城过来准备拉住她,你知道她说说了句什么?
蜜儿不光把语气模仿出来,连眼睛翻动的频率都学了出来,我有些畏惧的看着蜜儿,我感觉心里一个美好的形象正在蜜儿这个屠夫手下慢慢瓦解。
你是不知道她当初那傻样,我真是恨不得上去抽她一耳光。当然,阿城帮我出了口气,上去就是一耳光把她扇倒在地。
面对一个怨妇你要怎么解释?你给我解释解释看看,你说得倒轻巧,她那样蛮不讲理一上来就扯我胳膊我还要怎么礼貌?
我们俩坐在护城河边吹风,因为一两句的争执彼此都沉默了很久,阳光在中午的时候将护城河上的冰晒化了,我准备对蜜儿说句对不起,转眼看蜜儿低头拿着手机不知在干什么,我不知怎么开口才好。当我准备开口的时候蜜儿突然抬头对我说 出事了,出事了,赞哥被人打了,1947被人砸了。
我没反应过来就被蜜儿拖到了出租车上,她坐在后座焦急的握着手机,我一路叫司机加快速度,加快速度。蜜儿问我要不要打电话给阿城?我说到时候去了再说吧。
一路飞驰,车停在1947门口时我惊呆了,门口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几个警察在门口打电话,两辆警车停在后视镜里,我和蜜儿都有些不敢下车。
警察手中的塑料袋里装着凶手作案的蒙古刀,刀上还染着血迹。蜜儿一下倒在了我的怀里,警察说 先叫救护车,你是老板什么人?
我记得那天蜜儿被送上救护车后我有些眩晕,跟着警察到了酒吧里面的厨房,赞哥的一摊血迹还在地上,白净透亮的地板砖被一滩渗人的血红给霸占,像是一种无声的宣告,我被那一摊血迹给刺杀了,日后许多的日子里我都回不过神来,做梦梦见他还是小时候的样子,带着我满山奔跑,给我抓蛐蛐,蚂蚱,蜻蜓,我还记得我最爱的那只竹蜻蜓现在还摆在我的床头,只是我不记得他从什么时候长大的,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只为利益而不顾情谊的男人,从父母去世以后?从祖父将他赶出家门之后?还是从祖父离去我也只身一人来到城市以后?我那时才发现,原来他不是长大,也不是变化,只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已,而我学不会这样的保护,所以我需要他时不时对我的帮助,这样我才能更顺利的在这座并不欢迎我的城市中生活下去,当初我只是想要一份工作,没想到他却为了我努力开了一家酒吧,他为了我的梦想而付出了自己的心血,我没有为他而付出什么,当我接到医院的死亡通知单,我知道我之前所有的费解以及因为费解而生成的怨恨和抵抗都被一纸通知碾成了灰烬。
蜜儿住院了,医生说她严重贫血。无奈之下,蜜儿的爸妈从老家赶了过来,来的那天蜜儿还在生我的气,怪我瞒着她几把她爸妈叫了过来,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也懒得再解释什么。赞哥,她始终有些不相信,她说赞哥是个好人,就算是和她谈了恋爱也没有想过做什么过分的事情,不像有些风流鬼。我还未从赞哥的死亡中清醒过来,蜜儿看样子倒也没那么伤心,我想问的问题一直没有问出口,犹疑间病房的门被推开了,蜜儿的爸妈大包小包的进来了,我礼貌的打了招呼就出了门,不管蜜儿怎么对我使眼色我都出来了,我不习惯别人家的热闹和温暖,再有,我又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南方一下起雨来没有尽头似的,整个城市都湿漉漉的,我开车准备去往警察局的路上突然想起了邬靖靖,电话打通后邬靖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问她最近怎么了?问出口就后悔了,蜜儿才告诉我她自从那天的纪念日风波后一直萎靡不振。邬靖靖没吭声,我下意识问她她在干嘛,她的呼吸正准备带出一句话时电话断了,我的直觉中邬靖靖一定是遇到了困难,阿城的影子在我潜意识里带着模糊的光影,不管了,我将方向盘打回来,一路加速开往邬靖靖的家。
城北的烟草厂的小区里弯弯曲曲的小路太多,这一片全是年代感极强的老房子,邬靖靖家我只来过一次,还是几年前阿城生日邬靖靖邀请大家一起去她家给阿城庆生,阿城那天穿着别扭的西装,打着红色领带,远远看过去像个新郎官。蜜儿调侃他是个乡下暴发户。
我沿着小院子的左侧围墙走着,一只黑猫不知何时从旁边的小绿化带里窜了出来,停在我脚边时我推了一步,往后往前看了一眼发现居然没有,甚至没有一点声音。城市的喧闹一点没有在此体现,我装作凶恶的样子对着那只老黑猫跺了跺脚,吓得它又钻进了绿化带。后来到达邬靖靖家楼下才想起赞哥曾说过 如果遇见黑色的猫,别吓它,它不会怕你。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想得越多害怕得越多,进了楼梯间潮湿的台阶上出奇的滑,我记得是三楼的左手边,门上的缝隙里插着不知那年那月的艾蒿叶子,敲门的时候发现门居然没关,推开门口屋子里的黑暗叫人窒息,窗帘拉得死死的,不透一点光亮。邬靖靖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呼呼睡着,桌上的鲜花和长方形礼盒摆在茶几上,我轻轻打开礼盒,在打开礼盒前我走到窗户前拉开了窗帘,打开了窗户。盒子里呈放着一条手帕,手帕上写着 蒙古工艺 四个字,背面写着成串的蒙古文。
她撑起身子以一个慵懒的姿态仰面坐在沙发上,我环顾客厅里整齐干净,完全像是一个独居的女性的房间,她伸手向沙发侧面的箱子里,艰难的拿上来一瓶八宝粥递给我,我疑惑她的有气无力,她说 不好意思,家里只剩这个了。
她惊恐的把脚从地上缩到了沙发上,两条长腿弯曲在身前,下巴重重的放在膝盖上。像个不懂事的小女孩。
谁知道我这句话一出口她抱着一瓶八宝粥就哭起来了,我连忙接过她手里马上就要滑落的八宝粥,给她递上了那块手帕。
你知道我为了给他准备一个纪念日礼物,我把我所有的家底都花了,我爸现在在老家做心脏搭桥手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拿起那个长方形礼盒发现里面有张证书,我才想起原来礼物并不是什么手帕,而是一把蒙古刀。阿城确有收藏各种工艺刀的爱好,他曾说过他如果不做音乐他就会去开一个有关刀具的工艺品商店,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不敢再往下想象。
我不敢相信朝夕相处的阿城会对一个女人做如此粗鲁的事,邬靖靖的家里冷得要命,坐了一会我手就冰得吓人。她的手放到了我的手上说 你是不是冷?我去拿火炉。
我没准备把赞哥的死告诉她,她本应拥有一个专心诚挚的爱人,和她一样美好纯净的爱情,她不应该再经受任何现实给她的伤害,死亡是有种莫可名状的力量的,像段枯木被打进了心底,根本拔不出来。
我起身走时看见了她丢在茶几一角的两只袜子,我捡起两只白色的袜子转身过来时她已经睡着了,我走到她身边给两只冻得僵硬的脚套上,她脸上的安宁是大起大落后疲倦的缩影,我想我应该去为他讨回一些什么,我的心随着她怀中的胎儿的震动而沸腾起来,俯身正面她时她脸上的细节都摆在了我的眼睛里,细致的皮肤,毛孔,因为长久失眠生成的眼袋和黑眼圈,嘴唇是她最性感的地方,唇上的皱褶干裂了,渗出了血,血结了痂。
我关上门后并没有因为后悔放弃了一个亲吻她的机会而沮丧不已,现在的我需要理智来进行任何一项行动,下楼之后下起了雪子,一粒粒冰晶砸在脸上刺痛得让人颤栗。
梦做了许久,醒来后头痛欲裂,梦里的情节记不清一二,窗外的树梢上经过一夜的风雪满是雪白,树枝被压弯了身躯,玻璃上氤氲的雾气迷蒙,我伸手轻轻在玻璃上化了一张笑脸,屋外的银装素裹的景色透过一道明净的缝隙,我在成年之后有时不太喜欢大雪,喜欢阳光的时候比喜欢大雪要多得多。
雪夜,我根本顾不上有什么不妥,1947的一切都是属于我和他的,还有蜜儿,阿城。屋外的大雪没有停息的意思,风小了些,我从里面紧紧锁上门,把大厅里的灯全部打开,舞台上的灯亮起来的时候我几乎在一时间看见了当初第一次登上台的我,旁边是阿城疯狂的摇晃脑袋,舞台中的蜜儿甜蜜美好,和她的名字一样叫人对她不得心生爱慕。
我把柜台里的酒都拿了出来,酒不多了,摆在吧台上像极了一排排炸弹,我决定今夜我要尽全力喝下它们,它们是他留给我的遗物,如果不喝下它们,我不知道还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我对他的亏欠。
一杯接一杯,我想酒醉的午夜不来一些音乐根本不配来宿醉一场,从吧椅上下来时碰倒了桌上的一瓶芝华士,玻璃碎裂在地上的声音刺进了我的大脑,刚在迷迷糊糊中获取了些自在和洒脱,恍然清醒了过来,我立马端起了桌上的酒杯一饮而尽,我至今记不起我是怎么爬上了舞台,舞台上的话筒和话筒架的位置没有改变,我特意去摸了摸键盘,上面覆盖着一层灰尘。
齐秦的这首老歌是我多年来最爱的一首情歌,每次唱起它我就会想起一些凌乱又温柔的往昔,不过这次我借着醉意又一次在这个舞台哼起来时,我的眼前全是第一次的画面。
第一次来1947,第一次对赞哥说我要组乐队,第一次带着阿城和蜜儿来1947,赞哥配合我演了一出没有结局的戏码,第一次从阿城和蜜儿的眼睛里看见对音乐对梦想的渴求和希望,那时的我觉得无比满足,1947是我们三人追逐梦想的开始,我无法接受如今大家分崩离析的事实,酒劲在我的体内像一股比一股强劲的潮涌,拍打我的胸腔中最为软弱的地带。
我喷出了胃里未消化的秽物,躺倒在舞台中央,头上的五彩霓虹盖住了我的脸,我的身体,音乐还在耳边回荡,我能够想象窗外的大雪如何将整座本就冷漠的城市慢慢埋葬,冬天就此宣告降临,人们终究在孤独中掩饰孤独,世界在清冷的冬天成了一座孤独的宫殿,我准备慢慢睡去,以后如果还有机会醒来的话。
台下隐约的脚步声将我从梦中拉回,侧身面对台下一个模糊的人影,我对所有的鬼魂早已免疫了最恐怖的一面,渐渐地那个人影开始对我鼓掌,对我呼喊,我的意识里他应该不会是赞哥,如果是他他就会在台下大喊让我站起身来,然后再上来拥抱我。
睡过去后我忘记了一切,梦中我又回到了那个大雪纷飞的清晨,我对着雾气氤氲的玻璃窗滑下了一个简单的笑脸后,蜜儿打了电话给我,说阿城找了她,她说阿城现在像鬼一样落魄。找到她的时候阿城几天没有进食,在小饭馆里吃了十个馒头和一桶米饭,蜜儿当时被眼前这个饿死鬼一般的男人吓住了,然后他对蜜儿表白了,蜜儿在电话里说起这段恶心的表白差点呕吐。
蜜儿说她已经和阿城已经约好时间,晚上1947见。原来阿城这几天并没有在外逃亡,而是躲在1947的一个藏酒的地窖里,那个地窖联通着后门,从后门出来就是一片菜地,菜地几乎没有人去,阿城白天从菜地里挖些野菜,晚上偷溜倒厨房想办法弄熟它们。
蜜儿和我说完这些我不敢相信,不敢相信阿城居然真的成了一个丧心病狂的杀人犯,虽然在想象中我一度想过这种可能,不过等现实出现在面前时我还是无法面对,蜜儿说 阿城疯了,彻底疯了,廖儿,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害怕,我生怕他把我生吞了。
雪融化的第一天中午,我和蜜儿再一次坐到了护城河边,护城河的河水清灵灵的,有几只小渔船在远处飘摇,风吹散了树梢上的雪堆,散到了蜜儿的脖子里她抓住我的手臂直叫。
她瘪了瘪嘴,阳光依旧不肯放过亲吻她的脸颊,河边的风都被太阳照暖了,我眯起眼睛望向天空南归的燕子,它们从我们的头顶滑翔而过,一点没有离去时的伤心。
我不准备回答她这个问题,我也懒得追问她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秘密的。从兜里掏出一包彩苏,递给她一根,她看我不回答的气势有些赌气,接上烟后把头偏了过去。
烟点上了以后我觉得我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废人,前段时间我从自卑的心境中好不容易抽身而出,谁知道这么美好的氛围里再次被它拖了下去,我现在只想问出那个我没有对她问出的问题。河南治疗男科方法腿部淤青发紫怎么消除儿童咳嗽常吃的止咳药
- 下一页:共401字1页转到页编者按狂乱的心欢(1)
- 上一页:萧珊19181972(1)
最近更新
- 06月21日女生网空运宠物需要注意什么位置
- 06月21日女生网科蒙多犬狗狗品种介绍图位置
- 06月21日女生网秋田犬乱吃东西怎么办位置
- 06月21日女生网研究表明饲养宠物可缓解抚养自闭症儿童的压位置
- 06月21日女生网研究发现狗狗会面部识别同类位置
- 06月20日女生网可卡犬怎么洗澡知识位置
- 06月20日女生网可卡咬人吗不会随意去攻击人类位置
- 06月20日女生网可以给雪纳瑞犬吃人吃的饭菜好吗位置
- 06月20日女生网可以用肥皂给狗狗洗澡吗位置
- 06月20日女生网可以喂给狗狗零食和饭吃吗位置
- 06月20日女生网可卡犬价格血统和品相决定可卡犬的价格位置
- 06月20日女生网可卡犬乱吃东西怎么办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