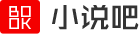奇幻
或者说只是记得他快如闪电的剑法
人们大约只是记得他在那个静悄悄的春夜里以及在那个凉风习习的秋夜里所做的事,或者说只是记得他快如闪电的剑法,只是认为他的那些事迹全来自一把剑,好像他身上如果不背着剑他就不存在一样;极少人知道他本从哪里来就好像如今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是不是还活在人世,在那两天里发生的事情淹没了他过去悲的喜的苦的乐的爱的恨的日子。似乎他是横空出世的,似乎他一出生就怀有无人能出其右的剑法,然后在那个月亮清幽的二月的春天里,在午夜犬吠时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六个武艺高强的人全杀了,然后又在那个红豆长成的秋天里把那个号称刀法第一的人打败了,——或许人们记得的只是这些,关于他的过去,关于他的出生,关于他的爱情故事,关于他的家族,人们毫无兴趣或者所知道的也只是凤毛麟角。大部分人说他出生在秋收黄澄澄的日子里,那年全县的庄稼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于是那些人就说他喜气洋洋地来到这块土地上就注定要戚戚惨惨地离开这块土地,这样他的生命才会和世界万物一样变得平衡——白天和黑夜一般长爱与恨一样深悲与喜一样多;只有几个人说他出生在冬夜里,他们说寒冷的天气造就了他阴郁的性格。即便大都赞成他出生在秋天,可具体日期却无人知晓,听说竟连他的父母也说不清道不明那是哪个月的哪一天。
他就这样给后人带来疑问地降落到这个世界上,就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问号,他就这样来到离县城这棵老榕树有十里地的古老村庄里。你可以骑马沿着酒店门前的这条官道一直往西走,在第一个叉路口往右拐,接着再一直沿着山脚的红泥路走,那里有一片片的桉树林,桉树林里偶尔参杂着几棵松树梧桐树,直到你看见一座大约百米长五米宽的石拱桥(那桥身长年攀爬着四季常绿的爬山虎,从桥头的石缝里伸出一棵大腿粗细的宽叶植物),到了那时你就看见那个村庄掩映在翠绿的龙眼树之间;你也可以搭上一叶扁舟顺着酒店后面的那条河绕过山抹过河滩经过或许不止九曲十八湾,当你看见第五个码头时也既是县里面最大的那个码头时,你也就看见他的祖宅了:那是一所百年的老宅子,那旁边的老榕树也已百年了。在一百多年前或者更早以前他的祖先带着他的妻儿带着他的族人历尽千辛万苦转辗来到这个河畔的村子,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上山运石头去树林里砍伐树木,在一个陌生的光秃秃的地面上创建了自己的家园,然后开垦荒地种植作物。也许最恶劣的并不是自然环境,而是当地人的冷漠鄙夷与排挤,他的祖先必定和村里想要把他以及他的族人赶走的恶霸流氓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开始与过程在逝去的岁月里凝结为一个僵硬的符号,时间慢慢把它风化剥除,即便是他那个作为胜利者的家族也已经没有人再去谈论那些陈年的旧事那些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家族值得骄傲与传颂的艰苦奋斗除恶扬善的精神了,那些人留下的唯有一座如今已灰绿塌陷虫孔斑驳的躯壳,直到在那个丰收的秋天里这个男孩降生。
的确没有人知道钟镜缘出生的确切日期,他的家族已经衰败到生亦何苦死又何哀的境地,铺张浪费的生日宴席也成了他们每个人既甜蜜又哀伤的回忆。他的那些曾光耀门楣的祖先们被集中安葬在西山脚下一个缓缓的荒草丛生的斜坡上,倒落在土地上似乎已经和土地融为一体的石碑记载着他们的丰功伟绩。他的高祖也既那个带领族人来到此地的祖先被推为里正,他的曾祖则官至县尉,他的祖父又被推为里正,而衰落也就是从他的祖父的后半生开始的。到了他父亲的时代,他便看不到什么辉煌的东西了。他的父亲只是一个镇里的私塾先生,一年的馆谷勉强能养活一家四口人,而他的叔叔伯伯们成了与牛与猪与鸡与鸭感情颇深的稍稍懂得武艺的地道的村舍汉。后来他的熟读四书五经的文人父亲染上了赌瘾,说起这个私塾先生村里的老人总是摇摇头把他的堕落归咎于那个孤芳自赏的出自赌徒之家的妻子,正是这个女人让他的父亲堕落了让他的家族陷入到那次鲜血淋淋的悲剧里。
钟镜缘带着一双忧郁的眼睛从娘胎里来到这样一个没落的世界当中,感受着没落的气息,触摸着年深日久的灰土,无奈地看着那个曾祖父兴建的现在已废弃的戏台,这个戏台曾上演了多少好戏呀!他就这样生存着,在一个没落的世界里和没落相伴左右,也许不曾有人为他把没落推开过,即使是那个如今躺在山脚那棵相思树下红泥地里的女人也没能把没落从他身边赶走,或者那个女人就不曾为他驱赶过那种感觉,她甚至是无情地在没落上添油加醋。关于那个女人,人们所知甚少,只是知道她有一个富有但神神秘秘的不知哪一年从哪一个地方赶着马车携家带口来到此地的父亲,他们住在东县城一个很深很深的连夕阳的余晖也照不进去的巷子里头。女人父亲的样貌或许还有人记得,可是女人的样貌却众说纷纭了。有人说她并不美丽,但却有一头能勾魂销魄的乌黑长发,一双大大的冷傲的眼睛;有人说她长得一般,鼻子不挺上嘴唇不薄,而且肤色是古铜色的;有人说她很美丽,圆圆的脸蛋窈窕的身姿,这个人说曾经看到钟镜缘和那个女人还有一个也是十八九岁的穿着华丽的男子一起在闷热的夏夜漫步在大街小巷里,这个人还说那个十八九岁的男子就是后来那个女人的丈夫。美与丑永远得不到证实了,她如今已再次化为了泥土培育坟墓旁的红豆,那些美丽的东西被腐蚀被分解支离破碎无影无踪,美与丑也只是剩下一句话一个传说了;她的家人她的丈夫的家人也不可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了,因为在那个杀气腾腾的本应喜庆的夜晚,两户人家三十六口人全成了一把刀下的鬼魂;她的那些朋友呢?直到今天仍不清楚她曾经有过哪些朋友,也没有人站出来说自己是那个女人的朋友。再也没有人知道钟镜缘与这个住在县城的富商的女儿是如何相识的了,兴许是一个季节的错误,兴许是一个街道的错误,又或者只是一首诗一个眼神一簇发稍一个笑脸的错误。也再没人知道他是如何坠入爱河的了,爱情和六月的雨一起沙沙的来了。可是谁都知道那只是他一个人苦等的爱情,那个女人也许至始至终都没有对他动过一丝一毫的爱情,也许即便她在地底下知道钟镜缘为她报了仇为她在墓畔植上了红豆也不见得会改变初衷。钟镜缘的爱情之树在春天不发芽长叶在秋天不结出果实,期间思恋的煎熬也唯有他自己最明了最深刻。那年他十八岁。村里的人发现,他的眼睛比以前更忧郁了,本应是天真无瑕的十八岁少年的脸如今是如此的沧桑仿佛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风霜。人们经常看到他骑着那匹棕色的母马跨过那座古朴的石桥穿过桉树林然后再从大榕树下酒店门前过去。即使是深秋的夜里仍有人看到他提着一个萤火虫般的灯笼在桥上漂过在树林里穿梭。他就在那个多雨的十八岁夏天坠入爱河了。然后夏天走了,秋天来打扫落叶迎接干干净净的冬天;接着是石榴花山茶花盛开的春天,接着知了在大柳树大榕树上鸣叫着夏天已来到;当空气中还保留着夏天的余温时,秋天又已在一阵梧桐细雨里显露头角了。那是发生在阴沉沉的八月的事情。那天早上有劳动能力的男人和女人都到野地里做农活去了,只留下小孩子们趴在路口的泥地里玩耍,后来他们长大了,他们回忆说那天早上他骑着马,身上什么也没有带,马背上什么也没有挂,他当时和平常一样的阴郁,可是面对小孩他还是露出了善意的微笑。他骑着马嗒嗒的走了,马蹄声是很清脆的;但是在劳作的人们还没有回家时他就回来了,他不再对小孩们微笑,他的母马显然很累了口吐着白沫,他显然让马剧烈奔跑过(这只有两种解释,一是为了赶路,二是为了发泄情绪而快马加鞭),马蹄声变得沉重拖沓了。他们好奇地看着他从他们面前过去,他的后背被撕了一道很长的口子,他们回忆说那是一道利刃划出的口子,口子很长平平整整,那或许是一把刀或许是一把剑。有人猜测他为了那个女人与那个同样出自富家的男人决斗了,结果他输了,后背的衣服被剑或者刀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同时也在他的内心划了一道长长的无法再愈合的口子。他就这样回到那座没落的老宅里,跟父亲也不说一句话就钻进自己的房间里把门关上,整整关了一个晚上。或许他把有关于那个女人所有的回忆都烧成灰烬或者全部封存,又或者把它们都打成了包袱带走了。到了第二天他就辞别了哭泣的父母辞别了那座没落的老宅以及里边住着的所有的人以及那个戏台那棵老树,他不知道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亲人的面貌:他们能够哭泣悲伤的面貌而不是死时狰狞不再变化的样子。他就这样离开了这个没落的地方,这回他骑的是那匹母马的小马驹,平时这匹小母马只拉去干农活。他就这样离开了,无人知晓他要去什么地方,也许甚至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他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了,在那阴沉沉的酝酿着风雨的八月里。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爱他的话那也只是他的双亲了,因此他的离去也只有他的双亲会悲伤;他那个时常和他争吵的妹妹巴不得他早点离开家眼不见心不烦呢!他的离开在村里可以说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母马不至于产不下马驹,母猪不至于形容枯槁,鱼塘里的鲤鱼也不至于一夜死光;人们只是在村头闲坐聊天时才轻轻地议论他的事,而时间一长他便被渐渐淡忘,取代他的又是另一个新奇的事情。山坡上的杜鹃春天一到照常开放,映红了整座山;那条离去的路径被风吹被雨打被日晒,路旁的植物和草被枯枯荣荣,就这样地过了三年的时间。在那年那个不安定的三月的夜晚,一场血腥的屠杀在那百年老树下在那百年老宅里在奄奄一息的门柱墙垣之间发生了,钟家十二口人无一幸免地躺在自己流出来的血泊中。全村没有一个人听到争斗的声音,阴霾的夜晚如墓地一般的平静。当时不懂内情的人纷纷猜测,只有手段高明武艺了得的江湖打手死士才能出手如此狠辣并且又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他们在那天晚上悄无声息地来,悄无声息地杀死了十二口人,然后又悄无声息地走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不久后凝固的血液和十二张痛苦狰狞的脸。捕快第二天中午才慢腾腾地来,他们也只是告诉人们那显而易见的情况:每个死者都是一刀毙命,有的被一刀槊死,有的被一刀割断喉咙;从伤口上看可能有六把不同的刀,也即是说可能有六个杀人凶手,其刀法在县里面可以说是数一数二。可是捕快只是告诉人们这些情况,等他们把现场清理干净后就又慢腾腾地走了,那几个凶手是谁他们从来不告诉人们,更不用说去缉拿凶手了;或者他们真的不知道是谁干的。不过很多村里的人知道大约是谁在那阴森森的夜晚制造了这起惨案,只是大家不敢在嘴巴上说出来而是在眼睛和心里互相默认。
直到萤火虫在夜晚低飞的四月的初夏,一个人坐着船来了。他是下午到的,当时妇女在码头洗菜男人往水桶里灌水孩子们在游泳,人们看到他站在船头,手里握着一把用破布裹住的大刀。他的姐姐在一个月前被杀了,因此他要再次来这里再次在船上下来。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他从前也就是在他姐姐嫁给那个私塾先生到被害的这段时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来这里探亲。后来发生了一次事故,他劫了一个商人的镖车而且杀了其中的四个镖师,他急匆匆来跟他姐姐拿了道了别就急匆匆地逃跑了,他姐姐也不知道他逃去何方。现在他带着一张黄昏般的脸回来了,而且手里紧握着一把大刀。他不知在这个码头登陆了多少回了,而今那些构成码头的石条有的崩塌掉到了水底,在水底长出墨绿的苔藓和水藻;有的在岸上被泥土覆盖,荒草在上面生根长叶。那天晚上一如平常的恬静没有任何值得传说的事情发生,萤火虫自由自在地在山脚下在已经播种的田野里低低地飞舞。据说那晚他也去村里的赌场赌博了,而且赢了一些小钱。不过有人说他就是在那晚把事情的真相弄清的,接着才有第二天晚上的故事发生——他带着刀一步一步走近赌场,月光在刀刃上闪闪发亮。那个长得象老鼠因此绰号叫老鼠的瘦小男人说了一声他来了就把赌桌掀翻从桌底下扯出一把刀来,然后窜了出去;紧跟着他身后也窜出了五个长相丑陋不是本村的男人,每个手上都抓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小不一的刀;于是这六个人在赌场外头在皎洁的月光下把他围住了。这也是一场赌博。在场观看的人无非赌徒闲汉,他们为搏斗下赌注。自然赌老鼠一方赢的占了绝大多数,因为一则他们人多势众,二则他们每一个都是江湖死士,三则假如他们真是杀害钟家全家的凶手那他们的刀法必然十分了得,就在一个月前捕快不是说凶手是县里面数一数二的刀客吗!听说也有赌那个孤军作战的人赢的,理由是当年他一把大刀砍杀了商人十二个镖师里面的四个,而且还能全身而退。观众越来越多了,妇女小孩也来了,他们躲在门缝里或者站在远远的地方观看。没有人因为一招半式而喝彩,关于这场生死搏斗人们记住的只是身影飘忽铁器铮鸣火花四溅刀光闪闪,以及最后躺倒在地上的人;人们凑过去看,他和他的姐姐一样死不瞑目。
经过这么一场战斗真相终于可以公开了:老鼠和那五个外来的刀客杀害了钟家十二口人。大概在两个月前,那个私塾先生又赌输了而且还欠了账,于是他就一筹莫展回到了家里央求他的妻子再给他些钱。可他一家确实是一贫如洗了,妻子无奈之下只能去找那个长相猥琐形如田鼠的人,不是去借高利贷而是去拿回之前借给老鼠的本属于私塾先生家的钱。争吵声说明她没有拿到那些钱,她哭着回来了,眼睛红红的,大约两个月后她就不再哭泣了,她和住在老宅里的其他十一个人一样躺倒在冰凉的水磨砖上死不瞑目。老鼠早就警告她准备四口棺材的,而钟家的男人也每天都在磨刀霍霍地准备着老鼠的到来。只是七个男人五个女人也不是老鼠还有那五个刀客的对手,刀光只一闪他们就注定活不了了。 共 9209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曾梦想仗剑走天涯”,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武侠梦,就是鲁迅先生也写过一个纯粹以复仇为主题的小说《铸剑》。这篇小说算是圆了作者的武侠梦,同时也表达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思想。小说中的“剑”既是爱情与复仇的象征,也是见义勇为的借代。里面的长句运用,有福克纳和克劳德西蒙之风格。【编辑:上官竹】
1 楼 文友: 2011-11-22 08:1 :27 邪不胜正,剑侠无敌。石壁上那把剑是正义的剑,惩凶治恶。自从那把剑插在石壁里的那天起,钟镜缘的故事就流传得更广。 联系QQ:1071086492
2 楼 文友: 2011-12-0 2 :5 :09 看到五月旧馆兄的这篇文章,突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而又有了一丝莫名落寞的伤感。石壁上的那把剑,是否就是您心中一直坚守、但却在现实中又虚无飘渺的正义?真理、麻木,这一切的一切都再您的小说中彰显,巧妙的构思,流畅的文笔,让小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楼 文友: 2011-12-22 1 :47:48 路过宝地,欣赏佳作,支持一下,得点实惠,呵呵,打搅了。宁夏妇科专科医院沧州妇科医院咋样辽宁妇科医院地址
他就这样给后人带来疑问地降落到这个世界上,就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问号,他就这样来到离县城这棵老榕树有十里地的古老村庄里。你可以骑马沿着酒店门前的这条官道一直往西走,在第一个叉路口往右拐,接着再一直沿着山脚的红泥路走,那里有一片片的桉树林,桉树林里偶尔参杂着几棵松树梧桐树,直到你看见一座大约百米长五米宽的石拱桥(那桥身长年攀爬着四季常绿的爬山虎,从桥头的石缝里伸出一棵大腿粗细的宽叶植物),到了那时你就看见那个村庄掩映在翠绿的龙眼树之间;你也可以搭上一叶扁舟顺着酒店后面的那条河绕过山抹过河滩经过或许不止九曲十八湾,当你看见第五个码头时也既是县里面最大的那个码头时,你也就看见他的祖宅了:那是一所百年的老宅子,那旁边的老榕树也已百年了。在一百多年前或者更早以前他的祖先带着他的妻儿带着他的族人历尽千辛万苦转辗来到这个河畔的村子,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上山运石头去树林里砍伐树木,在一个陌生的光秃秃的地面上创建了自己的家园,然后开垦荒地种植作物。也许最恶劣的并不是自然环境,而是当地人的冷漠鄙夷与排挤,他的祖先必定和村里想要把他以及他的族人赶走的恶霸流氓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开始与过程在逝去的岁月里凝结为一个僵硬的符号,时间慢慢把它风化剥除,即便是他那个作为胜利者的家族也已经没有人再去谈论那些陈年的旧事那些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家族值得骄傲与传颂的艰苦奋斗除恶扬善的精神了,那些人留下的唯有一座如今已灰绿塌陷虫孔斑驳的躯壳,直到在那个丰收的秋天里这个男孩降生。
的确没有人知道钟镜缘出生的确切日期,他的家族已经衰败到生亦何苦死又何哀的境地,铺张浪费的生日宴席也成了他们每个人既甜蜜又哀伤的回忆。他的那些曾光耀门楣的祖先们被集中安葬在西山脚下一个缓缓的荒草丛生的斜坡上,倒落在土地上似乎已经和土地融为一体的石碑记载着他们的丰功伟绩。他的高祖也既那个带领族人来到此地的祖先被推为里正,他的曾祖则官至县尉,他的祖父又被推为里正,而衰落也就是从他的祖父的后半生开始的。到了他父亲的时代,他便看不到什么辉煌的东西了。他的父亲只是一个镇里的私塾先生,一年的馆谷勉强能养活一家四口人,而他的叔叔伯伯们成了与牛与猪与鸡与鸭感情颇深的稍稍懂得武艺的地道的村舍汉。后来他的熟读四书五经的文人父亲染上了赌瘾,说起这个私塾先生村里的老人总是摇摇头把他的堕落归咎于那个孤芳自赏的出自赌徒之家的妻子,正是这个女人让他的父亲堕落了让他的家族陷入到那次鲜血淋淋的悲剧里。
钟镜缘带着一双忧郁的眼睛从娘胎里来到这样一个没落的世界当中,感受着没落的气息,触摸着年深日久的灰土,无奈地看着那个曾祖父兴建的现在已废弃的戏台,这个戏台曾上演了多少好戏呀!他就这样生存着,在一个没落的世界里和没落相伴左右,也许不曾有人为他把没落推开过,即使是那个如今躺在山脚那棵相思树下红泥地里的女人也没能把没落从他身边赶走,或者那个女人就不曾为他驱赶过那种感觉,她甚至是无情地在没落上添油加醋。关于那个女人,人们所知甚少,只是知道她有一个富有但神神秘秘的不知哪一年从哪一个地方赶着马车携家带口来到此地的父亲,他们住在东县城一个很深很深的连夕阳的余晖也照不进去的巷子里头。女人父亲的样貌或许还有人记得,可是女人的样貌却众说纷纭了。有人说她并不美丽,但却有一头能勾魂销魄的乌黑长发,一双大大的冷傲的眼睛;有人说她长得一般,鼻子不挺上嘴唇不薄,而且肤色是古铜色的;有人说她很美丽,圆圆的脸蛋窈窕的身姿,这个人说曾经看到钟镜缘和那个女人还有一个也是十八九岁的穿着华丽的男子一起在闷热的夏夜漫步在大街小巷里,这个人还说那个十八九岁的男子就是后来那个女人的丈夫。美与丑永远得不到证实了,她如今已再次化为了泥土培育坟墓旁的红豆,那些美丽的东西被腐蚀被分解支离破碎无影无踪,美与丑也只是剩下一句话一个传说了;她的家人她的丈夫的家人也不可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了,因为在那个杀气腾腾的本应喜庆的夜晚,两户人家三十六口人全成了一把刀下的鬼魂;她的那些朋友呢?直到今天仍不清楚她曾经有过哪些朋友,也没有人站出来说自己是那个女人的朋友。再也没有人知道钟镜缘与这个住在县城的富商的女儿是如何相识的了,兴许是一个季节的错误,兴许是一个街道的错误,又或者只是一首诗一个眼神一簇发稍一个笑脸的错误。也再没人知道他是如何坠入爱河的了,爱情和六月的雨一起沙沙的来了。可是谁都知道那只是他一个人苦等的爱情,那个女人也许至始至终都没有对他动过一丝一毫的爱情,也许即便她在地底下知道钟镜缘为她报了仇为她在墓畔植上了红豆也不见得会改变初衷。钟镜缘的爱情之树在春天不发芽长叶在秋天不结出果实,期间思恋的煎熬也唯有他自己最明了最深刻。那年他十八岁。村里的人发现,他的眼睛比以前更忧郁了,本应是天真无瑕的十八岁少年的脸如今是如此的沧桑仿佛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风霜。人们经常看到他骑着那匹棕色的母马跨过那座古朴的石桥穿过桉树林然后再从大榕树下酒店门前过去。即使是深秋的夜里仍有人看到他提着一个萤火虫般的灯笼在桥上漂过在树林里穿梭。他就在那个多雨的十八岁夏天坠入爱河了。然后夏天走了,秋天来打扫落叶迎接干干净净的冬天;接着是石榴花山茶花盛开的春天,接着知了在大柳树大榕树上鸣叫着夏天已来到;当空气中还保留着夏天的余温时,秋天又已在一阵梧桐细雨里显露头角了。那是发生在阴沉沉的八月的事情。那天早上有劳动能力的男人和女人都到野地里做农活去了,只留下小孩子们趴在路口的泥地里玩耍,后来他们长大了,他们回忆说那天早上他骑着马,身上什么也没有带,马背上什么也没有挂,他当时和平常一样的阴郁,可是面对小孩他还是露出了善意的微笑。他骑着马嗒嗒的走了,马蹄声是很清脆的;但是在劳作的人们还没有回家时他就回来了,他不再对小孩们微笑,他的母马显然很累了口吐着白沫,他显然让马剧烈奔跑过(这只有两种解释,一是为了赶路,二是为了发泄情绪而快马加鞭),马蹄声变得沉重拖沓了。他们好奇地看着他从他们面前过去,他的后背被撕了一道很长的口子,他们回忆说那是一道利刃划出的口子,口子很长平平整整,那或许是一把刀或许是一把剑。有人猜测他为了那个女人与那个同样出自富家的男人决斗了,结果他输了,后背的衣服被剑或者刀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同时也在他的内心划了一道长长的无法再愈合的口子。他就这样回到那座没落的老宅里,跟父亲也不说一句话就钻进自己的房间里把门关上,整整关了一个晚上。或许他把有关于那个女人所有的回忆都烧成灰烬或者全部封存,又或者把它们都打成了包袱带走了。到了第二天他就辞别了哭泣的父母辞别了那座没落的老宅以及里边住着的所有的人以及那个戏台那棵老树,他不知道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亲人的面貌:他们能够哭泣悲伤的面貌而不是死时狰狞不再变化的样子。他就这样离开了这个没落的地方,这回他骑的是那匹母马的小马驹,平时这匹小母马只拉去干农活。他就这样离开了,无人知晓他要去什么地方,也许甚至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他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了,在那阴沉沉的酝酿着风雨的八月里。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爱他的话那也只是他的双亲了,因此他的离去也只有他的双亲会悲伤;他那个时常和他争吵的妹妹巴不得他早点离开家眼不见心不烦呢!他的离开在村里可以说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母马不至于产不下马驹,母猪不至于形容枯槁,鱼塘里的鲤鱼也不至于一夜死光;人们只是在村头闲坐聊天时才轻轻地议论他的事,而时间一长他便被渐渐淡忘,取代他的又是另一个新奇的事情。山坡上的杜鹃春天一到照常开放,映红了整座山;那条离去的路径被风吹被雨打被日晒,路旁的植物和草被枯枯荣荣,就这样地过了三年的时间。在那年那个不安定的三月的夜晚,一场血腥的屠杀在那百年老树下在那百年老宅里在奄奄一息的门柱墙垣之间发生了,钟家十二口人无一幸免地躺在自己流出来的血泊中。全村没有一个人听到争斗的声音,阴霾的夜晚如墓地一般的平静。当时不懂内情的人纷纷猜测,只有手段高明武艺了得的江湖打手死士才能出手如此狠辣并且又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他们在那天晚上悄无声息地来,悄无声息地杀死了十二口人,然后又悄无声息地走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不久后凝固的血液和十二张痛苦狰狞的脸。捕快第二天中午才慢腾腾地来,他们也只是告诉人们那显而易见的情况:每个死者都是一刀毙命,有的被一刀槊死,有的被一刀割断喉咙;从伤口上看可能有六把不同的刀,也即是说可能有六个杀人凶手,其刀法在县里面可以说是数一数二。可是捕快只是告诉人们这些情况,等他们把现场清理干净后就又慢腾腾地走了,那几个凶手是谁他们从来不告诉人们,更不用说去缉拿凶手了;或者他们真的不知道是谁干的。不过很多村里的人知道大约是谁在那阴森森的夜晚制造了这起惨案,只是大家不敢在嘴巴上说出来而是在眼睛和心里互相默认。
直到萤火虫在夜晚低飞的四月的初夏,一个人坐着船来了。他是下午到的,当时妇女在码头洗菜男人往水桶里灌水孩子们在游泳,人们看到他站在船头,手里握着一把用破布裹住的大刀。他的姐姐在一个月前被杀了,因此他要再次来这里再次在船上下来。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他从前也就是在他姐姐嫁给那个私塾先生到被害的这段时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来这里探亲。后来发生了一次事故,他劫了一个商人的镖车而且杀了其中的四个镖师,他急匆匆来跟他姐姐拿了道了别就急匆匆地逃跑了,他姐姐也不知道他逃去何方。现在他带着一张黄昏般的脸回来了,而且手里紧握着一把大刀。他不知在这个码头登陆了多少回了,而今那些构成码头的石条有的崩塌掉到了水底,在水底长出墨绿的苔藓和水藻;有的在岸上被泥土覆盖,荒草在上面生根长叶。那天晚上一如平常的恬静没有任何值得传说的事情发生,萤火虫自由自在地在山脚下在已经播种的田野里低低地飞舞。据说那晚他也去村里的赌场赌博了,而且赢了一些小钱。不过有人说他就是在那晚把事情的真相弄清的,接着才有第二天晚上的故事发生——他带着刀一步一步走近赌场,月光在刀刃上闪闪发亮。那个长得象老鼠因此绰号叫老鼠的瘦小男人说了一声他来了就把赌桌掀翻从桌底下扯出一把刀来,然后窜了出去;紧跟着他身后也窜出了五个长相丑陋不是本村的男人,每个手上都抓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小不一的刀;于是这六个人在赌场外头在皎洁的月光下把他围住了。这也是一场赌博。在场观看的人无非赌徒闲汉,他们为搏斗下赌注。自然赌老鼠一方赢的占了绝大多数,因为一则他们人多势众,二则他们每一个都是江湖死士,三则假如他们真是杀害钟家全家的凶手那他们的刀法必然十分了得,就在一个月前捕快不是说凶手是县里面数一数二的刀客吗!听说也有赌那个孤军作战的人赢的,理由是当年他一把大刀砍杀了商人十二个镖师里面的四个,而且还能全身而退。观众越来越多了,妇女小孩也来了,他们躲在门缝里或者站在远远的地方观看。没有人因为一招半式而喝彩,关于这场生死搏斗人们记住的只是身影飘忽铁器铮鸣火花四溅刀光闪闪,以及最后躺倒在地上的人;人们凑过去看,他和他的姐姐一样死不瞑目。
经过这么一场战斗真相终于可以公开了:老鼠和那五个外来的刀客杀害了钟家十二口人。大概在两个月前,那个私塾先生又赌输了而且还欠了账,于是他就一筹莫展回到了家里央求他的妻子再给他些钱。可他一家确实是一贫如洗了,妻子无奈之下只能去找那个长相猥琐形如田鼠的人,不是去借高利贷而是去拿回之前借给老鼠的本属于私塾先生家的钱。争吵声说明她没有拿到那些钱,她哭着回来了,眼睛红红的,大约两个月后她就不再哭泣了,她和住在老宅里的其他十一个人一样躺倒在冰凉的水磨砖上死不瞑目。老鼠早就警告她准备四口棺材的,而钟家的男人也每天都在磨刀霍霍地准备着老鼠的到来。只是七个男人五个女人也不是老鼠还有那五个刀客的对手,刀光只一闪他们就注定活不了了。 共 9209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曾梦想仗剑走天涯”,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武侠梦,就是鲁迅先生也写过一个纯粹以复仇为主题的小说《铸剑》。这篇小说算是圆了作者的武侠梦,同时也表达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思想。小说中的“剑”既是爱情与复仇的象征,也是见义勇为的借代。里面的长句运用,有福克纳和克劳德西蒙之风格。【编辑:上官竹】
1 楼 文友: 2011-11-22 08:1 :27 邪不胜正,剑侠无敌。石壁上那把剑是正义的剑,惩凶治恶。自从那把剑插在石壁里的那天起,钟镜缘的故事就流传得更广。 联系QQ:1071086492
2 楼 文友: 2011-12-0 2 :5 :09 看到五月旧馆兄的这篇文章,突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而又有了一丝莫名落寞的伤感。石壁上的那把剑,是否就是您心中一直坚守、但却在现实中又虚无飘渺的正义?真理、麻木,这一切的一切都再您的小说中彰显,巧妙的构思,流畅的文笔,让小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楼 文友: 2011-12-22 1 :47:48 路过宝地,欣赏佳作,支持一下,得点实惠,呵呵,打搅了。宁夏妇科专科医院沧州妇科医院咋样辽宁妇科医院地址
- 下一页:p指尖的灵魂p
- 上一页:终于学会了如何爱你原创
最近更新
- 06月21日奇幻秦大妈在网上发帖声讨虐狗行为位置
- 06月21日奇幻秋田犬刚回家要怎么照顾位置
- 06月21日奇幻秋田犬与柴犬的区别是什么位置
- 06月21日奇幻研究称人狗情关键在眼睛眼神激发爱的荷尔蒙位置
- 06月21日奇幻科学喂养阿拉斯加雪橇犬的方法位置
- 06月20日奇幻可卡幼犬三个月的可卡幼犬价格及科学饲养方位置
- 06月20日奇幻可卡价格常见可卡犬都是以黄色系列为主位置
- 06月20日奇幻可以科学有效的训练贵宾犬的小技巧位置
- 06月20日奇幻可以培养狗狗安静休息的训练方法位置
- 06月20日奇幻可以利用奖励来训练苏格兰牧羊犬位置
- 06月20日奇幻可卡犬什么时候开始换毛位置
- 06月20日奇幻可卡犬不小心把塑料袋吃了没事吧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