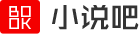诗人杨炼荣获2018意大利南北国际文学奖
意大利“北-南国际奖”评委会把2018年“Premio Internationale NordSud” (北-南国际奖)颁发给中国著名诗人杨炼。
意大利“北-南国际奖”评委会把2018年“Premio Internationale NordSud” (北-南国际奖)颁发给中国著名诗人杨炼。今年是该奖颁发第十年,奖项为国际文学奖一名,国际科学奖一名。5月18日在意大利Pescara举行颁奖典礼。
人物介绍
杨炼 (1955—),中国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生于瑞士,文革中开始写作,朦胧诗最早作者之一,198 年以长诗《诺日朗》轰动大陆诗坛,1988年后环球漂泊,追求建立“诗意的他者”之自觉。2012年获诺尼诺国际文学奖(Nonino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Prize),201 年获首届“天铎”长诗奖,2014年获卡普里国际诗歌奖(The International Capri Prize2014)。201 年应邀成为挪威文学暨自由表达学院院士。2008年至2014年任国际笔会理事。现任汕头大学驻校作家暨讲座教授。现居柏林与伦敦。
获奖感言
感谢意大利“北-南国际奖”评委会把2018年“Premio Internationale NordSud” (北-南国际奖)颁发给我。今年是该奖颁发第十年,奖项为国际文学奖一名,国际科学奖一名。5月18日在意大利Pescara举行颁奖典礼。我已写就受奖辞《不让这首诗沉沦为冷漠死寂的美》,将在典礼上宣读。诗歌,聚焦思想的深度、语言的力度和形式的精美,我这场“以百米短跑速度跑出的马拉松”,仍在继续。
作品选读
大海停止之处
(一)
1
蓝总是更高的当你的厌倦选中了
海当一个人以眺望迫使海
倍加荒凉
依旧在返回
这石刻的耳朵里鼓声毁灭之处
珊瑚的小小尸体落下一场大雪之处
死鱼身上鲜艳的斑点
像保存你全部 的天空
返回一个界限像无限
返回一座悬崖四周风暴的头颅
你的管风琴注定在你死后
继续演奏肉里深藏的腐烂的音乐
当蓝色终于被认出被伤害
大海用一万枝蜡烛夺目地停止
2
现实再次贬低诗人的疯狂
一个孩子有权展示一种简短的死
火焰使众多躯体下降到零度
恨团结了初春的灰烬
花蕊喷出的浓烟越是宁静越是傲慢
一厢情愿的纯洁的恐怖
这一天已用尽了每天的惨痛
火呛进肺叶时
海水看到母亲从四肢上纷纷蒸发
去年的花园在海上拧干自己
在海鸥茫然的叫声中上升到极点
孩子们犯规的死亡
使死亡代表一个春天扮演了
偶然的仇敌黑暗中所有来世的仇敌
仅仅因为拒绝在此刻活着
单调的与被单调重复的是罪行
一个独处悬崖的人比悬崖更像尽头
你被上千吨蓝色石块砸着
眼睛躲不开砸来的大海
那看见白昼的与被白昼剥光的
时间死者放肆的
一根鱼骨被打磨得更尖不可能是错误
一滴血稀释了怀抱沉船的水
象牙过时而残忍像一座阳台
树木又住自己枝头绿色的鱼群
这间雪白病房里雪白的是繁殖
袒露在屋顶上狂风
改变每只不能够粗暴的手
天空的两腿被床栏固定
给了海大海在睡梦中更无知地滑动
一只蟑螂抽搐得酷似人类
过去的与被过去吐出的只是肉
这现实被你记起只有远去的肉
否定一座蓝色悬崖
否定了翅膀的大海早已被摔碎
你脸上每个波浪写下光的谎言的传记
而盯着尽头的眼睛是一只鲜牡蛎
正无尽地返回隔夜坏死之处
大海停止之处
(二)
1
铺柏油的海面上一只飞鸟白得像幽灵
嗅到岸了那灯塔就停在
左边我们遇难之处
铺柏油的海面上一只锚是崩断的犁
一百年以墓碑陡峭的程度
刷新我们的名字
在红色岩石的桌子旁被看着就餐
海水碧绿松叶的篝火让骸骨取暖
呲出满口锈蚀发黑的牙跳舞
小教堂的尖顶被夹进每个八月的这一夜
死亡课上必读的暴风雨
那光就停在更多死者聚集之处
锚链断了锚坠入婴儿的号哭深处
情人们紧紧搂抱在柏油下
一百年才读懂一只表漆黑的内容
2
花朵的工事瞄准了大海
一只等待落日的啤酒杯涂满金黄色
像嘴唇上逐渐加重的病情
那说话的在玻璃上继续说话
那歌唱的都被一把电吉他唱出
用十倍的音量封锁一个聋子
微笑就是被录制的
食物掰开手指
水手溺死的侧影就逼近
在椅子和椅子之间变成复数
风和风是呼吸之间一滩咸腥的血迹
那被称为人的使辞语遍布裂缝
石头雪白的脚踝原地踏步
使心跳的楼梯瘫痪
日子既不上升也不下降就抵达了
最后的醉鬼的被反刍的海
麻痹的与被麻痹裹胁的年龄
沉船里的年龄
这忘记如何去疼痛的肉体敞开皮肤
终于被大海摸到了内部
被洗净的肝脏一只白色水母
被腌熟的脸牵制着上千颗星星
被海龟占领的床 仍演奏发亮的乐器
当月光无疑是我们的磷光
潮汐不停地刮过更年幼的子宫
呼救停进所有不存在的听觉
在 鲨鱼被血激怒前静静悬挂的一刹那
我们不动天空就堆满铁锈
我们被移动大海的紫色阴影紧握着
一百年一双喷吐墨汁的手
摸无力的与被无力实现的睡眠
耻辱骑在灯塔上
摸死者为沙滩遗留的自渎的肉体
飞鸟小小的弓把飞翔射入那五指
我们的灵柩不得不追随今夜
挖掘被害那无底的海底
停止在一场暴风雨不可能停止之处
大海停止之处
(三)
1
谁和你在各自的死亡中互相濒临
谁说惟一被丰收的石头
使海沉入你的水下
当你看时只能听到鸟声就是葬礼
你听却梦见海的暗红封面
搁在窗台上
噩梦把你更挑剔的读完
尸首们被再次回忆起来的白垩填满了
谁和你分享这痛哭的距离
现在是最遥远的
你的停止有大海疯狂的容量
孤独的容量让一只耳朵冥想
每个干枯贝壳里猛兽的鲜血在流尽
雪白剧毒的奶一滴就足够
给你的阳光哺乳
睁开眼睛就沦为现实
闭紧就是黑暗的同类
2
这类似死亡的一刹那 的一刹那
黑色床单上的空白同时在海上
中断的一刹那肉体
用肉体的镜子逃出了自己
焚烧的器官是一条走廊
而瘫痪是使大海耀眼的湛蓝目的
女孩们欢呼放弃停止存在时
最鲜嫩的窗户都湿漉漉被海推开
投入一个方向没有的方向
远离弹奏的手指琴本身就是音乐
远离风盐住进全部过去的伤
类似被遗忘的仅仅是现在
正午的黑色床单上一片空白 的水
血缘越远越灿烂照亮了堕落的一刹那
现在里没有时间没人慢慢醒来
说除了幻象没有海能活着
无力生存的也无从挽回了
大海集体的喘息中
名字被刨掉敏感的核
指甲抵抗着季节谋杀彻底不朽
鸟翅扇凉了形象
谁的与被谁用一个梦做出的
停止在现在的与被停止无痛改变的
你总是你的镜子更邪恶的想象
缺席者更多时更是世界
每一滴水否定着充满视野的蓝
死亡坚硬的沙子铺进夜晚的城市
一条人物的烂鱼
是肮脏的影子就一定能再次找到产妇
而谁听见别人在耳鸣
现实才敞开像一门最阴暗的知识
这不会过去的语言强迫你学会
回顾中可怕的都是自己的
脸被墓地辉映时都是鬼魂的赝品
历史被秋天看着就树干银白
噩耗一模一样的叶子
彼此都不是真的却上千次死于天空
大海锋利得把你毁灭成现在的你
在镜子虚构的结局漫延无边之处
大海停止之处
(四)
1
King Street一直走
Enmore Road右转
CambridgeStreet14号
大海的舌头舔进壁炉
一座老房子泄露了
无数暗中监视我们的地点
我们被磨损得剥夺得再残破一点
影子就在地址上显形
陌生的辞仅仅是诅咒
近亲繁殖的邻居混淆着
死鸽子呕吐出一代代城市风景
玻璃嵌进眼球
天空就越过铁道骄傲地保持色盲
每个人印刷精美的废墟的地图上
不得不拥有大海
所有不在的再消失一点
就是一首诗领我们返回下临无地的家
和到处被彻底拆除的一生
2
海浪的一千部百科全书打进句子
岩石删去了合唱队
没有不残忍的诗
能完成一次对诗人的采访
寒冷从雪白皮肤下大片溢出
灌木引申冬天的提问
总被最后一行掏空的
遗体总是一只孵不出幼雏的鸟窝
一个早晨墙壁上大海的反光
让辞与辞把一个人醒目地埋在地下
一首诗的乌云外什么也不剩
谁被自己的书写一口口吃掉
像病人被疾病的沉思漏掉
一部死亡的自传用天空怀抱死者
没有不残忍的美
没有不锯断的诗人的手指
静静燃烧在两页白纸间形成一轮落日
说出说不出的恐惧
某个地址上孩子切开一只石榴
某个地址把孩子想象成
眼睛肉里白色的核
血凝固成玻璃的吱吱叫的鸟儿
一半躯体在手中看不见地扭动
而牙齿上沾满被咬破的淡红色果冻
死孩子看到了
那忘记我们的与被忘记无情复原的
一座入夜城市中抽象的灯火
是再次却决非最后一次
剥夺我们方向的与被太多方向剥夺的
蓝总弥漫于头颅的高度
在凝视里变黑
总得有一个地点让妄想突围
让构成地址的辞习惯人群的溃烂
空虚 在眼眶里
仅仅对称于
大海在瞎子们触摸下没有形状
某个地址指定种植银色幽香的骨头
剥开我们深处
孩子被四季烘烤的杏仁
成为每个
想象被看到否定的
被毁灭鼓舞的
石榴裹紧蓝色钙化的颗粒
大海从未拍击到孤独之外
从未有别人在悬崖下粉身碎骨
我们听见自己都摔在别处粉身碎骨
没有海不滑入诗的空白
用早已死亡的光切过孩子们停止
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
制作拼团小程序平台
微商城单品怎么做
微信怎么开通小程序
饭后恶心精神焦虑抑郁消化不良肠胃敏感注意什么好
孩子感冒能吃优卡丹吗
- 下一页:云水因为你爱上她小说
- 上一页:三体作者刘慈欣用文字表现科幻是迫不得已
- 06月21日奇幻秦大妈在网上发帖声讨虐狗行为位置
- 06月21日奇幻秋田犬刚回家要怎么照顾位置
- 06月21日奇幻秋田犬与柴犬的区别是什么位置
- 06月21日奇幻研究称人狗情关键在眼睛眼神激发爱的荷尔蒙位置
- 06月21日奇幻科学喂养阿拉斯加雪橇犬的方法位置
- 06月20日奇幻可卡幼犬三个月的可卡幼犬价格及科学饲养方位置
- 06月20日奇幻可卡价格常见可卡犬都是以黄色系列为主位置
- 06月20日奇幻可以科学有效的训练贵宾犬的小技巧位置
- 06月20日奇幻可以培养狗狗安静休息的训练方法位置
- 06月20日奇幻可以利用奖励来训练苏格兰牧羊犬位置
- 06月20日奇幻可卡犬什么时候开始换毛位置
- 06月20日奇幻可卡犬不小心把塑料袋吃了没事吧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