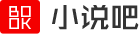流年内心苍狼巴丹的个人生活四章
一、亮色
越过戈壁,在沙漠深处,我们可以看得更远,只是那些松软的黄沙,平静的起伏,却有着埋葬的危险和吞噬的杀机。刚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这里面还有人居住、工作和生活。
从我们所在营区出发,出营门,就是戈壁滩了。一丛一丛的骆驼刺漫无目的地生长着,根茎上结满尘土,裤脚或者手掌稍微一触,就抖起一团浓浓的灰尘。夏天时候,傍晚,我们总是要去那里散步,几个一伙,踏着硬硬的沙石,抬头是西冲的落日,以七色的晚霞作为陪伴;低头是黑色的碎石,动物的足迹和地鼠的幽深洞穴。
而要到那个小点,需要乘车,三十公里的路程足够一台解放和北京吉普跑一个多小时。车轮一旦接触到戈壁,灰尘就起来了,虽然有一条车子压了不知多少遍的路,但很多的地方浮土厚重,一些经验不足的司机经常在它们那里抛锚。其实,什么事情都一样,熟能生巧,跑得多了,司机就了如指掌了,跑起来得心应手。车子大幅度地颠簸着,我们紧握着扶手,全身崩了劲儿,不使自己身体碰到一边的钢铁。即使这样,脑袋也难免碰到车顶,一下一下的,令人猝不及防。
即使密封程度再好的车子,也阻挡不了无孔不入的细尘,这些善于钻营的投机者,只要稍微有点缝隙,绝对不会放过。但也不可排除车子本身的问题,很多东西根本上是内部的原因。在这样的路上,我们几乎没有闲暇左右看看,目光盯紧前方。不断迎面而来的戈壁,在我们的凝望之中,始终是一种无动于衷的姿态,仿佛临危不惧的勇士,面对迅速奔来的钢铁,没有一丝的惊惶和不安。
其实,一条路就是一种过程,既是肉体的也是生命的。接近的时候,那个小点就出现了。在昏黄色的戈壁当中,数株绿树,掩映着数座雷达和光测塔罩。在这二者之间,灰旧的营房显得尤其低矮。营门很窄,只可以容一辆卡车勉强通过。也没有战士站岗,想来也不需要,这沙漠的纵深地带,除了领导和机关的人,一般不会有什么人来。两边的红砖墙上写着一些口号和标语,最显眼的当数“身在沙漠,志在蓝天”和新近的“三个代表”了。看着那些红艳艳的大字体,我心里就有点激动,在一色枯燥的沙漠,多一种颜色就多一份生机,至少也是一种填补。营区里面,是两排左右正对的房子,正西是饭堂。两边是一色的杨树,绿油油的叶子在风中不断地忽闪着,拍打着。院子很宽,篮球架和排球各占一边。许多的战士只穿了背心和短裤,在场上叫喊着,奔跑着,左冲右挡,闪跃腾挪,小小的篮球和排球在空中飞来飞去,煞是热闹。
这时候,正是200 年的五一放假期间,不仅任务繁重,而且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自然灾害。我们没有惊扰他们,倒是一个在一边看球的战士飞身跑回营房,不一会儿,教导员郭广彬出来了,快步走到副站长冯治国面前,立正,敬礼。我就在一边站着,看见郭广彬的脸上,丰盈着一种喜悦和激动的笑容。张口对我们说,一个月没有见到外面的人了,语气里面有些遗憾和感伤。说着就把我们往大队部领。走到门口的时候,一个小男孩蹦跳着从里面跑了出来,看到我们,飞快地冲我们喊了伯伯和叔叔。不用告诉,我们也知道这是郭广彬的儿子。冯副站长说,一家人都到这儿来了。郭教说是的。
其实,我在政治处工作的时候,写过关于这个小点的典型事迹材料,其中专门提到了郭广彬的夫人马冬艳。郭广彬到这个单位任教导员两年多了,每当小孩放假,夫人马冬艳就带着来到小点,与郭广彬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我们深知,对于常年生活和工作在沙漠深处的官兵来说,对于异性,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情。记得我在另一个小点的时候,还偷偷地在戈壁滩上写过一些至今想起脸红的话。对此,我不以为有什么错误,至少是一种生命的自然和本真欲求。马冬艳的到来,无疑给这个小点带来了一抹亮色。时间一长,相互熟悉了,官兵把轻易不说出的秘密都说给了马冬艳,主题内容无外乎请嫂子介绍对象之类的个人私事。马冬艳听了,也记在心上,回到师部所在的营区之后,穿针引线,两年时间,促成了几对,其中两对已经结婚,还在三对正在进行中。
说完了这些闲话,我们这次来的任务也快完成了。临走的时候,郭广彬和马冬艳一直送到营门口。走了一段路程,我再回首,他们还站在路边,朝我们看。看着他们逐渐变小的身影,突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情绪,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在我的内心,缭绕着,游动着,遍生感慨。
二、南沙山
一抬头,就看见它了。在营区内,我从宿舍出来,走出一段柳树的排列,转身,向东,抬眼,它就在那里。更多的时候,它是静止的,在沙漠上面,微微隆起,与我们的目光保持平视,视觉绵软,内心亲切。
每天早上和傍晚,是它最美的时候,尤其是夏天,太阳刚刚升起,光芒打在我们身上,温和、均匀而散漫,耀着领章和帽徽,连同眼睛,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发光物件里面,都晃动着一颗太阳。目击的南沙山,也满身金黄,就连背阴的凹陷处,也丝绸一样披散。
风在沙漠的腹腔还没睡醒,鼻息幽微。这应当是风对我们的一种仁慈,不忍再打搅我们被它撕扯了一宿的心情,也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忘却和改善心情的机遇,以坚定我们日复一日在它一边生活和工作的信心。这里面似乎含有一种欺骗和诱导的意味,但我们已经习惯了,也愿意接受。而南沙山,作为一种流沙的流浪和积攒,它的皮肤不断更换,从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或者百里之遥,或者就在身边,更多的沙子来历不明,像我们一样,阅历简单,而方向多变。
我们知道,它是流动着的,沙漠和风运动的结果,只是觉察不到。多少年了,它的姿势不曾改变,这是在我们的感觉和眼光。事实上,它不断运动,变小、扩大,每时每刻,就像我们的年龄、职务和心情。我经常感慨,内里的流动,往往与表面联系不大。就像我和我们,很多时候,内心惊涛骇浪,樯倾楫摧,但脸色仍旧一潭止水。
作为一个人,谁的心里会没有风呢?
风在人的内心,蟒蛇一样的硕长、柔韧,我们并不清楚它们的首尾具体何向。
作为一种仅在咫尺的风景,一种事实,实际上也是一种安抚。每年的“五四”,我们都要去一趟,算是春游。在沙漠,在这个军营,除了南沙山,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的呢?这似乎有点狭隘和残忍。但好在有一处令我们产生欲望的风景,这多少是一种对长期枯燥心灵的勾引乃至滋润。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名叫巴丹 的沙漠边缘,我们常常遗憾,近处的戈壁和远处的沙漠过于平坦、粗砺、毫无起伏和一览无余了,即使有心仪的女子,可连一个约会,甚至偷情的地方都不予施舍。
出了营区大门,彩旗飘起来了,在我们的肩头和头顶,在戈壁之上,蓦然一片嘹亮,歌声响起来了,在空廓之中,溅不起一丝声响,尽管声音在我们的嘴巴和胸腔,有着雷和风的动静。脚下的粗沙和碎石,身边的骆驼刺和梭梭草不断摇晃着蓬开的身子,细碎的尘土犹如戈壁喷吐的烟圈。平时不多见的沙鸡和野兔在前方或者一侧,突突飞起,仓皇奔跑。我们打搅了它们的安静,它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对此,我们大概没有歉疚,我们由来已久的自大、麻木习性,根深蒂固。
戈壁褪去,就是一色的黄沙了,高高低低,依次隆起,一直到了需要仰望的高度。背后是蓝得要命的天空。一顶一顶的沙丘,硬硬的,挺挺的,光洁的,干净的,时常忍不住要抚摸。我时常为这一念想感到羞惭,但又一想,太多的无力的美,似乎用来摧残的。这时候,阳光炽烈起来,提升着黄沙的温度。沙子从鞋口涌入,双脚发烫,行走在火焰之上的感觉,我们索性脱了鞋子,光光的脚丫,在平静的沙坡之上留下伤疤,一道一道,扭曲得叫人心疼。但我们也似乎没有觉察,到达顶点的欲望占据了心情,我们喊着,跑着,一个个撅着屁股,扭着粗细不一的腰肢,气势有点像攻占高地,样子却类似笨猴爬杆。我在后面,气喘嘘嘘,全身的汗水拧着肢体。
至山顶,截然一面刀刃,曲曲弯弯,好一道优美的线条。一边是幅度平缓的沙山,一边则是刀切一样的深渊,足有三百米之深。深渊的一边,就是干硬的戈壁了,一直向北,伸展着辽远。而向南的一面,沙坡起伏,沙丘连绵,一座一座,诗歌一样的沉着、幽静、闲适和优雅,有着无意炫耀的意味和随其自然的开放姿态。而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包括我们留在其上的那些脚印和躺倒的痕迹,也许就在今晚,就会消失得跟没有一样。我们都想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留下一些自己的东西,而什么东西才是真正能够留住的呢?沙漠、戈壁乃至它们造就的这座沙山,有一天也会消失,所不同的是,它们的消失我们无法看见,而我们的走远乃至消失却在它们的目睹之下。
旗帜更为猎猎了,风在鼓荡着它们的单薄的躯体,我们把它们插在沙领上,坐在下面,照相、喝水、吃东西,大声说笑。这时候,我敢肯定,每个人都是快乐的,我们的快乐基本源于这座沙山。而沙山快乐吗?我们不得而知。返回的时候,我们排成队列,从一侧刀切一般的深渊,贴着浮沙滑了下去,松软的黄沙载着我们的身体,连同手中的旗帜,从至高处到最低处,仅仅几分钟的时间,而其间的感觉,有一些快感,有一些惊惧,回首仰望的时候,还有一些莫名的感伤:向上和向下,速度、心情、方向和结果泾渭分明,内心惊诧,但无法出声。
三、内在的果实
2005年春天,几天来,我一直看见能够看到杏花和梨花,在夹杂了尘土的沙漠风中,持续地暗暗开放。与之相邻的杨树和沙枣树稍微迟钝一些,连绿芽都没萌出。少有的杏花开得粉红,阳光温暖,它们在正午的妖艳光泽,让周边高大的树木感到羞涩。每次路过,我都会停下来,盯着满树的杏花看(似乎重温旧年的爱情);再把鼻子凑近,它们的香味还是去年的(印象中的香味,贯穿杏花的一生)。
紧接着,梨花开了,一身的花朵。白天,它们是大地的脂粉;而晚上,则素洁异常。花朵的蓬勃味道在空中,苏醒的蛇一样,轻盈而又懵懂。有很多次,我近距离地看到它们:灿烂的花片和花蕊竟然是惨白的,微卷的;似乎一张张皱褶的面孔。没过多久,一夜风吹,这一年的梨花就再也不再了,连同落在地上的花片,也会在瞬间杳无踪影。
然后的果实,从花朵的废墟中探出来。很早之前,我就知道,这里的杏树果实叫李广杏——以我倍加推崇的汉代将军李广命名,简单的果实,而因了这个名字,除了文化之外,还有沧桑的时光味道——悲怆的鲜血和长矛硬弓,个人武功和卓越品格……一个人,除了史书外,还被这样一种果实所传承,该是怎样的荣幸?李广杏味甜,汁多,据说还有治疗咽喉肿疼、醒神和开胃的功效。内核则坚硬,杏仁很香,满口生津……每年五月,我都可以吃到。只是,还没开口,就想起那位“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的盖世将军。有时候会伤感:人不在了,尸骨成灰——将名字和故事交给这样的一种承载和流传——时间、世事、抑或灵魂的不朽,总叫人迷茫而又欣慰。
而这里的苹果梨树,则是变种,一个外来者的形象,梨子和杏子混合的形状让我匪夷所思。前些年,第一次吃的时候,心里蓦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混血的果实,满含的汁液似乎白色的鲜血。据当地人说:这里的苹果梨树是早年从青海或者宁夏嫁接过来的——两个地方的树木,因为一根枝条,而变成了另一种树木……苹果梨树冠盖庞大,叶子呈椎圆形,树干黝黑泛红,其中有些类似雀斑的白色斑点,密密麻麻,从树根到树梢,均匀密布。
年幼的时候,杏子和苹果梨都是苦涩的。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杏子小,酸,软,不用费大的力气,就可以咬开;那种酸,犹如北方的酸枣,甚至有过不及。怀孕的妇女很喜欢,刚刚小指头肚大,就嚷着叫老公摘几个吃(我看到的妇女们几乎都吃得津津有味,连一点酸的皱纹都没有泛起)。苹果梨则是坚硬的,表皮发青,再坚硬的牙齿,再大的力气咬下去,也只是一道浅浅的牙印。
杏花之后,是梨花。梨花之后,才是苹果花――白色的花朵,包着一层粉红的表皮,类似西北高地上的女人们脸上普遍的“高原红”。而我知道情况是:巴丹 的苹果树也是外来的(有人说:苹果是最民主的水果),起初是跟随着人的手掌和脚步,现在是飞速的车轮。这里土质粗糙,含碱量大,再好的苹果树种永远也长不高,果实类似小孩子拳头,直到十月匍降白霜,叶子卷曲,呈焦黑色,仍还高悬枝头。清晨,果实坚硬,用手一摸,便可感觉到一种刺骨的冷。
这里的枣花有两种:大枣花和沙枣花。它们根本区别是:大枣由人在自家的果园栽种,果实属私有。沙枣为野生,果实为公有。大枣大致原地山东或河北(巴丹 沙漠以西的绿洲和村落,大都不是原住民,从方言看,大致来自山东、河北、陕西、内蒙等地),花是米黄色的,颗粒细小,密布枝桠间,掩住伸出的长刺。有人说,最好的蜂蜜就是出自枣花,但这里似乎没有很多的蜜蜂,大都是大黄蜂和小黄蜂。这些不知来自何处的生灵,从不成群结队,而是单独一只,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飞走了又来了(事实上,我根本无法判定是不是先前的那只)。
共 7616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巴丹 的个人生活》是一个散文系列,以个人经历为基本线索,描写了作者在茫茫沙漠中的生命体验和独特思考。 本文选取了其中的四则。【亮色】写的是沙漠的纵深地带的一个小小的营地,那里几乎与世隔绝,每当孩子放假,教导员的妻子马冬艳就带着孩子来营地住一段时间,她成了荒凉大漠的一抹亮色。【南沙山】南沙山是营地的一处风景,每年的“五四”,作者和战友们都要去那里春游,它以它独特的沙漠风情给人们一种心灵的寄托和抚慰。【内在的果实】沙漠戈壁中,偶尔也有花朵和果实,看着它们开花、长叶、结果、成熟和衰落,便想到生命的顽强与坚韧和生生不息。【沙漠的田野】沙漠里也有绿洲。在这里,夏天是最美的,棉花次第开放,芦苇在风中起舞,村庄和村民们忙忙碌碌。这是沙漠的另一种风景。文章对自然事物及人生观察细致入微,描绘逼真,处处表现出对生命的独特感受和思考。艺术手法也很新颖,既师承传统散文的写法,也揉进了现代的艺术元素,值得学习、借鉴。!问好作者!祝你创作愉快!【:燕剪春光】【江山部精品推荐01 0 1806】
1楼文友:201 -0 -17 21:19:52 文质兼美的散文,学习了!
感谢你对流年的支持!问安! 有花皆吐雪,无韵不含风
2楼文友:201 -0 -18 07:42: 4 品文品人、倾听倾诉,流动的日子多一丝牵挂和思念;
灵魂对晤、以心悟心,逝水的时光变得更丰盈和饱满。
善待别人的文字,用心品读,认真品评,是品格和品位的彰显!
我们用真诚和温暖编织起快乐、舒心、优雅、美丽的流年!
恭喜,您的美文由 逝水流年 文学社团精华典藏。
感谢您赐稿流年,祝创作愉快! 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相逢,用文字找寻红尘中相同的灵魂。
微信商城系统
商城系统开发
新零售小程序
汉森四磨汤适用人群女人便秘吃什么能调理
腰酸背痛如何锻炼
- 下一页:中国各省省名之由来
- 上一页:荷塘拜水定去都江堰随笔
- 06月21日现实称职犬主在爱犬需要时出手位置
- 06月21日现实科普母猫不孕不发情的五大原因位置
- 06月21日现实秋田犬为什么不能养野性是主要原因位置
- 06月21日现实研究称狗祖先来自中国南方或通过丝绸之路迁位置
- 06月21日现实科学家带你一起揭开猫喝水的秘密位置
- 06月20日现实可卡犬左眼有很多黄色的眼屎该怎么办位置
- 06月20日现实可卡吃什么对毛好位置
- 06月20日现实可以给贵宾犬喝牛奶吗位置
- 06月20日现实可以导致吉娃娃死亡的一些原因位置
- 06月20日现实可以和宠物狗睡觉吗位置
- 06月20日现实可卡犬什么时候注射疫苗才好位置
- 06月20日现实可卡犬不慎误食异物怎么办知识位置